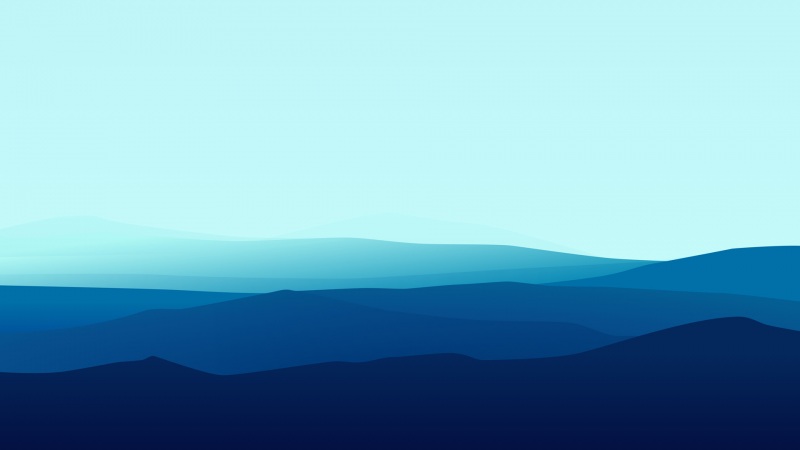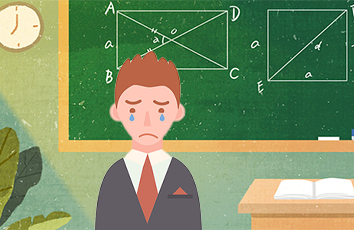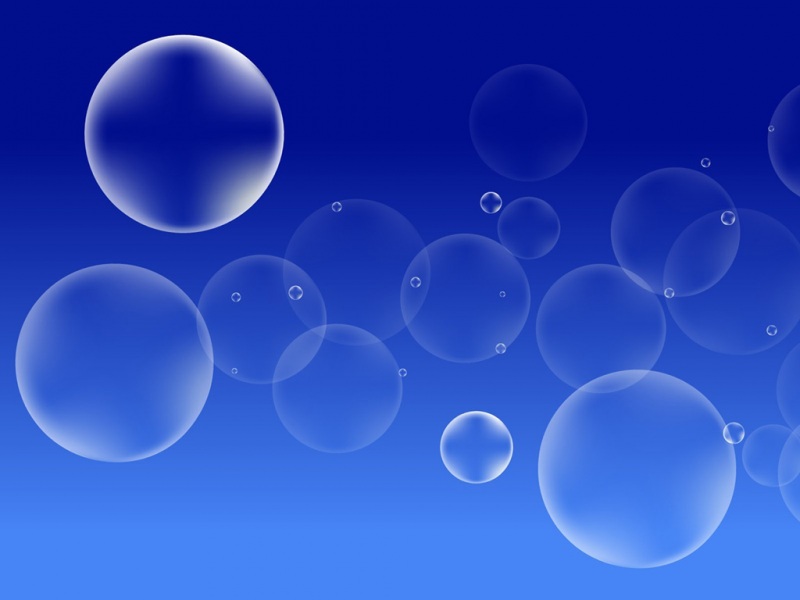父 亲
亦青子
今年父亲节以来,心里不时想写点关于父亲的文字,虽然父亲已经逝去十几年了,但我仍然经常想起他和有关他的一些事来。
父亲的童年是艰难困苦的,小时候听母亲说过,他两岁丧父,三岁随我奶奶的再嫁来到正阳楼内,由于他从小懂事,很得继父的疼爱。听奶奶说过,父亲那时只上了三个晚上的夜校,可由于他思想的进步及自学成才能力,至18岁时,他就参加土改工作,后来还当上了大队长,让土生土长的正阳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在他3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随着整个国家命运的跌宕浮沉,父亲也曾几次被打倒,经受人生的几起几落。也许正是这些起起落落的人生历练,才使得他在我们兄弟们的记忆里,活现成一条富有远见、遇事不惊的铮铮硬汉。
父亲21岁那年,经人介绍与母亲结了婚,婚后十几年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父母亲在无意间相继生下9个儿女。记得那时,老老少少十几个人口住在四间低矮的旧瓦房里,三代人合睡在两张半的旧式大床上。那时的我、还有几个弟妹跟奶奶睡在一起,经常睡梦中翻身,总感觉满床都是大大小小的脚丫。现在回想起那时的炎热夏天,在如此的窗小屋低,蚊多帐破,没电没风扇的生活环境中,人是怎么睡得着的呀?
从那时起,父亲就责无旁贷地成了这个簇拥着三代人、十多个人口的家庭的无可替代的顶梁柱了。眼看着孩子一个个出生和长大,父亲在措手不及之时,总是变着法子渴望养活一家人。种植业、养殖业里的辛苦活,他几乎都尝试过。种过辣椒、烟草、蘑菇……也养过蜜蜂、猪、鸭等等。在那仅靠两肩挑水、双手耕犁的年代,一年四季酷暑寒冬,除非村里有事,父亲总是在田地里忙活,餐风露宿早出晚归。母亲心疼,每当父亲下地干活去的时候,总记得给他另倒一壶稠点的粥,盖好壶盖放到灶台一边,生怕父亲很晚回来,孩子们胡搅后的饭缸里的地瓜粥更稀更冷,又会惹起父亲的老胃病。
记得那时父亲经常犯胃疼,几次看到他从田地里回家后,手捂着肚子曲着身子坐在木凳上闷不作声的模样,母亲喊他吃饭,他也只是头也不回地摇摇头的样子。父亲如此这般年复一年地昼夜劳作、忍饿挨疼,也就是希冀能通过他的苦心经营,盼能对家庭的生活有一丁点的改善,然而,在我的印象中,他那些年的手胼足胝,呕心沥血,似乎也没给家里带来太大的收成,不仅生产队里的超支大户帽子一直难于摘除,家里的生活也仍然困苦不堪,唯一多了的是他那双鬓的一茬茬白发,虽然那时我们兄弟都还小,但已经非常懂得心疼父亲,总希望自己能快快长大,能早日帮父母分担生活担子,让父母不再那样的辛苦劳累。
即使是这样,父亲也一直咬紧牙关背负着极大的经济压力让子女们读书,这是他在乡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曾经有多少人多少次对他说,生活这么苦,孩子读书有啥用,还不如早日让他们出来帮忙挣工分?父亲总是态度坚定地说不,“孩子会读书,再困难也要让孩子一直读上去”。这是他每次遇到不同的人讲同样问题时他回答的同样的一句话!为了这句话,多少年啊,父亲从来都是一边忙着村里社外的活,一边要算计着家里日常的柴米油盐,还有过年过节、人情世事、孩子学费等。等到家里有了半点收成,他就得掐着指头计算好,再过多少天孩子上学了,农历那天又做节来了……别人可以啥都不想地过日子,他可不行。而让父亲最头疼的是,口袋子里半个月摸不着一毛钱,而必须开销的事儿却都如约而至,一件也不会少。遇到这时,父亲总是思忖着该向那一家去开口最能借到钱,一经有了目标,他便晚饭后早早出门,总是先到大队部旁边阿九伯烟杂店又赊了一包烟,只吩咐一声“记下吧”便转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去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年的春节过后,父亲的眉头又紧皱起来,母亲悄悄对我说,你爸又在为你们的学费发愁了。那是开学的前一天夜里,外面风很大,还下着蒙蒙雨,因为天冷,大家都早早躲进被窝里。不知道是啥时辰,睡梦中我被 “吱呀”一声推门声吵醒,随着,父亲走了进来,轻轻叫了一声:“妈,睡了么?借到了”,父亲的声音虽小,但那极大的喜悦瞬间弥漫整个小屋。接着是“嘶嘶”两下划火柴的声音,“借了两主,才凑齐了”。父亲说着,已点着了挂在墙壁上的小油灯。奶奶翻了个身,随声应道:“借到了?那就好,那就好”,随之左手撩开蚊帐,看着油灯下正在低头数钱的父亲,又心疼地说了一句“天很晚了,去睡吧”。我知道,父亲说的是天亮后孩子们的学费的事,他回家后的第一时间来到奶奶的房间,是想把这份喜悦连夜传递给奶奶,也让她老人家这一夜安心地睡足眠。那天晚上,我的心五味杂陈,一时间无法入睡,想了很多,很远。
父亲的操劳和坚持,我们儿女辈都看在眼里,在当时,兄弟们共同的心愿就是一定要用功学习,把书读好。值得父亲欣慰的是,兄弟五人都很会读书,上厅的两面斑斑驳驳的墙壁上糊满不同年级的大大小小的奖状,
但至今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尽管学校里的书读得再好,也无法从书本里获得那时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所得到的太多的知识和见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有无数个这样的场景,晚饭后,油灯前,庭院里,我们兄弟们围着父亲,听他讲人生的道理,生活的故事;讲人要打拼,要勤劳勤俭;讲对人要好,憨人有憨福;讲生活体统,待人礼貌。大至人生道理,小至餐桌上规矩,他都老生常谈,谆谆以教,以至于我们兄弟姐妹们在后来的生活中无以忘怀而获益终生。在当时,大哥应该也才十几岁,小妹也只是六七岁,而我们似乎都很懂事,一点都不觉得父亲牢骚烦人,反而是巴望父亲晚上少出门,能够在家多和我们聊聊天,不厌其烦地听他讲那些人生和生活的道理。
父亲也有很严厉的时候,还是在我十岁出头的时候,有一次村里一个玩伴偷偷主动借我5分钱,然后拉我去赌博,被父亲知道了,等我输光钱回家后,他竟然抓住我连骂带绑地把我双手捆绑起来,吊在院里的横梁上,以此惩戒我。幸亏三弟人小胆大,趁父亲吃饭去,给我偷偷松绑,我才得以逃脱。那天晚上,我都不敢回家睡觉,被隔壁堂哥知道了,拽我到他家睡去。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去赌场了。直到那年大年三十母亲给了我2角的压岁钱时,我才去还了人家的那5分钱。
就这样的日子,父亲以他那坚挺的腰杆硬背着这十几个人口的生活重荷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直到1976年,这一年是我们的国家大事频发的一年,也是我们家大事连连的一年。这一年父亲又一次被宣布当了大队副书记,接着是76岁的奶奶病逝,随后是大哥被保送上了大学。也是在这一年我高中毕业,时年17岁,便被父亲叫去离家15公里的祖马林水库工地当记工员。每天12分的工分、每月有45斤的粮票和15元的收入,如此的待遇在当时不亚于一个公社干部。但时间不长,记得77年入秋的一天下午,父亲从老家踩着自行车到水库工地来,见了我便说:“昨晚四中的朱教导到俺家来,说是明年全国恢复高考,学校筛选了近几届高中毕业生中书读得比较好的60名学生,要举办高考补习班,有你的名,你回去不?”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要回去!”我知道,朱教导亲自到家告知此事,主要还是念及父亲老交情,其次才是我中学那几年书念得还好的因由。
四十几天的补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记得非常清楚的是77年的12月16日,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的第一天,那天父亲起得特别早,特地交代母亲说,得捞几碗干饭给我吃。我晓得父亲的用意是让我高考这两天临时享受下不吃大锅稀饭的特供,再者也是考虑到考场少走厕所的因素。母亲意会,并多做了一道萝卜炒蛋菜,还在旁叮嘱我慢慢吃多吃点。待我吃饱饭刚放下碗,就听见父亲从上厅大声叫我:“吃好了么,过来喝几杯茶再去。”我应声转身,未进厅门,便看到上厅屋里弥漫着丝丝烟雾,还透着一股炭香味,蒙雾中父亲正蹲着身子,对着火碳炉用力煽着火,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回过头来对着我说“时间还有着,水快开了,我泡茶,你喝几杯后再去,吃干饭,你考试就不会口干”。我站在厅前,目注着父亲那左右摆扇使劲煽火的背影,鼻子一酸,眼睛一下子湿润了。那时的我,强烈地感觉到此时此刻父亲给予我的期待,全身顿时有一股力量在涌动,我攥紧拳头,对自己说,一定要考好,要考上!
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当年父亲为我烧碳泡茶的那背影的时候,我就不由地会想起儿时那许多关于小火炭炉的故事来。记得那时,每当客人来时,父亲总是喊着:“孩子们,有人在吗?生火。”然后在家的我们都会应声而至,很乐意地开始熟练地清理碳屎,找来刨木花并用手揉成圆球状,用火柴点燃并迅速放进碳炉里,待刨木花完全燃开后,再挑几个松脆点的木炭轻轻放进去,紧接着便要迅速但须轻轻地煽动竹扇,待到先放下的木炭已完全着火燃烧起来时,才能再往碳炉里添进足够的木炭,然后便可放上装好水的烧壶,再用力煽起扇子来,也只有到这时,你才能够一边轻松地摆着风,一边翘起耳朵时不时抬起头来听大人们说话了……所有这些记忆,全因父亲的角色,而成为我们成长中难以忘怀的脉动。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家的生活随着大哥、我参加工作和三弟退伍回家创业后而慢慢好起来。到1984年后,四弟也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五弟则又考上中山大学研究生继续深造。他们俩是81年参加高考同年考上的大学,记得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公社领导还专门到家送笔和笔记本、还有每人15元的钱,以资鼓励。上学那天,村里还组织了锣鼓队一路“咚咚锵、咚咚锵”地送到车站。那时的我,才真的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光荣!
一晃几年过去了,四弟五弟也都快大学毕业了,可以预见,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的家庭已在悄然发生改变,很快如经过漫漫黑夜的太阳一般快要喷薄欲出了!记得也是这一年,正月刚过,有一天父亲把我们成家后的兄弟仨叫到一起,说:“古人言,树大分叉,你们三人都成家了,我想近日找个好日子,把你们分了吧,各自去发展,会好很多。老四老五他们也都快出来了,往后生活也不用担忧的。”听父亲这话时,虽然一时觉得很突然,但心里还没多大介意,直到农历二月初十那天,母亲按照家乡的风俗,给我们兄弟仨新家庭都准备一锅地瓜饭端过来的时候,我的心才慌了起来,心酸得不行,眼泪也簌簌地往下直滴,一下子接受不了兄弟们从“咱家”到“你家”的过程。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这是父亲在家庭生存发展史上又一个很伟大的决策,有如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对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般的英明决策,体现父亲那时审时度势后的智慧和远识。84年的兄弟分家,是每个小家生活状态开始好转的标志,是家族经济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更是兄弟们先后不失时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体制保障。
那时的大妹子也已嫁人生子,家里还有七妹、九妹和父亲母亲一起生活,早年送给古雷西林的八妹也偶尔回来小住几天,因此,父母亲也不会因为孩子们的分家而感到清静,相反倒是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觉得生活的担子一下子轻松了很多。这时的父亲,也已经是年过半百,黑瘦的脸上不知不觉中已刻上许多忽深忽浅的皱纹,两腮的颧骨及尖尖的下巴显得更加的骨感,不要说头上的白发,就是嘴巴上下的胡须也早已黑白参杂,而近年看报纸时越戴越深的老花镜更让父亲常常发出“老了,没办法了”的感叹,但即使是这样,这时候的父亲在别人的眼里,是更加的精气神了,每天看到他都是有说有笑、眉头舒展的样子,从前经常复制在脸上的忧愁样和失眠状已经没有了。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我们兄弟仨为退伍在家待业的三弟想到一个创业项目急急跑去跟父亲商量,想不到当时父亲听完后,对我们说:“你们兄弟想好、能办得了的事,你们就去做,今后让我动脑筋的事,再不要了。”是啊,父亲显然是累怕了,他可能也想,你们也都成家了,该有决定事情、支撑家庭的能力了。是啊,他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是当了多年的大队长了,是大队里几百户几千个人口的“家长”了。而现在,他想退休了,不管事了。大概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在乡里的那种备受尊重的优越感和喜气样也更加被乡亲老友称赞传扬,每当村里村外熟人一见面,听到“龙兄你好命啊,一门四进士,下半辈子吃不完了”,父亲总是喜形于色地回答:“是啊,还不用考虑吃的啦。”然后便从上衣袋里掏出烟来递过去,算是作为人家说好话的酬报。那个时候,随着子女们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父亲抽的烟也不断从“牡丹”提升到“红七匹”,又很快进入“阿诗玛”阶段,每个阶段基本上都跟得上“干部烟”的档次,这也是他最知足最享受最引以为傲的生活内容之一。有一次我和大哥劝父亲把烟戒了,没想到他竟然说:“我养你们九个子女的时候,我抽得起烟,现在你们九个子女养我一个人,让我把烟戒掉,没那些事!”他这句话竟让我们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从此,再也没有对他提过戒烟的事,相反却是在常常回老家时,总记得带几包好烟回去。父亲一见好烟总是眼睛一亮,急急收下,转身走到厅角挪开那大谷缸盖子把烟埋进缸里的谷子里去,然后再把盖子移回去。他一个人总舍不得现抽,等到老友来时,他便会神气兮兮地弯下身从大缸谷里摸出一包来,用手抹去烟壳谷尘,然后又用小指甲轻轻地挑开烟口金箔,有规则地慢慢撕开其中半边烟纸,露出排列整齐的烟支,然后拿近鼻子,深深吸闻一下,再用中指从烟底拱出二三根烟支来,轻轻抽出一根,递过去,说道:“这是老几带回来的,香!”看到老友眼珠老久不移地盯着香烟的摸样,父亲的脸上写满得意。而我们一时倒也觉得,这应该成为我们为之创造的场景之一。
至今我都还没全想明白,在那年代,一个如此家境如此平凡的父亲,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真情相见的朋友?让如今何止衣食无忧,甚至坐拥香车豪宅的现代人常常感叹知友难寻而冥思苦想答案渺茫。在那计划经济时代,父亲每次到镇上去时,经常会带回一些由粮站和供销社凭条供应的面粉、米糠、糖油、布等特供品。记忆中镇里供销社的云龙伯、王伯、春熙叔、照哥,还有公社的洪社长、老蔡叔、合德叔等,不管是家里做节还是平常日子,时常能看到镇上这些“当干部”的社会人物到家来找父亲泡茶聊天、吃年节的身影。门口停着的自行车总是让邻居和路过的乡下人探头探脑,心中总犯嘀咕。经常也看到父亲傍晚时分从镇里小醉回家,然后向母亲炫耀说早上去赶街先去那里泡了好茶然后又到那里喝了几杯啥啥酒等等,而母亲从来不喜欢他喝太多的酒,口里总会唠叨几句,还干她的活去。记得父亲和母亲吵嘴最经常的是做节的时日,一大早,父亲总是起早出门,不一会儿,便一手提着整排猪排骨、肝、肚等,一手提着沉甸甸的猪肉回来。母亲一见,就脸红声大地嚷了起来:“嘴里说没钱,一出去就又赊了那么多,以为你好使有得赊,不用还钱是不?”母亲还不是这样说了算了,经常一唠叨就半个时辰,气得父亲直咬牙胡须都快竖了起来,考虑到年节日子,他也只得忍气吞声,顶多说一句“你说吧,继续说”。我们小孩站在一边不敢作声,倒是希望这时有客人来,就会立即平息战事,重拾节日欢喜气氛回来。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次做节那天上午,父亲的几个老友都会不约而至,早早准时到家来帮忙打面,这似乎成为这群老友们各自做节时的一个必须的常规节目。早餐后,父亲就会叫我们找来火碳炉准备烧水,他自己则会把一大袋的面粉先搬到下厅的餐桌旁,然后把专为节日准备的上好烟茶各拿出一包来,自己先撕开香烟抽出一根来点上,待到老友有人来了,父亲就开始泡茶,也就是一支烟的功夫,三四个老友也就差不多都到齐了,然后便有说有笑,开始点燃节日气氛。待到大家几根烟抽完了,父亲便会喊大家开始干活,于是所有的大手都分工明确地活动了起来,身强力壮的九寥伯负责搓面团,推车出身的林火伯负责擀面,身材瘦小的维伯则专门负责切面,父亲则是一边把切好的面送到火房去给母亲煮熟,一边泡茶侍候大家。记得那时老家每年做节的次数约有三、四次,每次做节单是面粉就要准备四、五十斤,能够让客人吃到面子的人家在当时算是很有面子的家庭,“很有面子”一词大概也是由此而出。等到半百斤的面粉都擀好切好了,也差不多是午饭时分了,母亲则会用煮猪肉的汤给每个人现烫一大碗新鲜的面吃,父亲则会不顾母亲反复强调的那些肉都还没拜拜的理由,硬叫母亲弄几样现成的肉菜。待到面和菜上来时,几个老友也就全忘了半天的辛苦,围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吃上两大碗肉面,然后才各自回家去了。临走时父亲总会再三吩咐“晚上要早点来啦”,因为家乡做节,主餐都在晚上。不同村落的做节时日都是该社里所供奉的神明的生日或忌日,因此大多不在同一天,这样每逢做节时日,亲戚朋友都会相互走动,请来请去,借此饱餐一顿以解久馋,也是增进关系联络感情的时机。有些姑姨舅妗还专门带着几身衣服过来,大有长住几天之意,让女主人嘴上说好,心里气得很,脸上一时堆满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你如果认为父亲这样的朋友只是做节吃吃喝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的印象中,无论父亲是风光还是落寞,是春暖还是冬寒,父亲的这些朋友都是那么的真挚而平淡,温暖而知心。朋友间不管那家有了什么事情,该帮啥子忙,他们总会心知肚明,竭尽所能,带来慰籍,给予接济,这种醇厚的感情无时无刻不体现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中,让人温暖几辈子。记得一年冬天,也好像是三月初三年节快到的时候,一天晚上约9点多,父亲晚饭后出去溜了一圈后回来,我和大哥还亮着油灯在上厅八仙桌旁看着书,见父亲回来,我马上让座,父亲坐下后直搓手,显然是外面很冷冻僵了手,脸上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收起书本,问父亲泡茶不?他嗯了一声,说你们若也想喝,就泡吧。我急忙找来火炭炉,开始生火。父子仨也就边等水开边聊起天来。这时,借着油灯照出的光线,但见庭院门外十几米处一个黑乎乎人影正往家门口走近来,父亲睁大眼睛轻轻说:“好像有人来坐?”话音刚落,那人已踏进庭院门来,我和大哥异口同声叫了出来:“维伯。”只见维伯右肩膀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进屋后双手从肩膀上把袋子摔了下来。父亲一下子就知道,那是米,大米!只听见父亲明知故问:“你大冷天三更半夜拿啥来得?”维伯拍拍腰间的谷尘,一边坐到大哥让座的椅子上,一边对父亲说:“三月初三快到了,你有米吃么?”父亲看着老友,苦笑了一下,便转移话题,问我“水开了吗?泡茶”。我和大哥都知道,维伯家人口也多,本不好过,家住青阳院,是在几公里外的山下,这样冷的黑夜,记住我家做节,徒步背米送来,这种老友知意之情,何止雪中送炭可表!
好在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84年我们兄弟们分家后,都相继离开乡下,搬到镇里去住。那几年,是父亲最惬意的生活时光,每天他都自由自在地过着,大概两三天他就会骑着自行车到镇里来,因为我们排前成家了的兄弟仨均住在镇里的同一条街上,相距不上一公里。父亲来了,总是老大家泡泡茶,再到老二家坐坐,又到老三家看看,儿媳们的孝顺在镇里村里也是有口皆碑的,见他来,真心高兴,好烟好茶侍候。父亲便一边沏茶,一边聊起家常来。待到晌午时分,不管在谁家,他都可以很随意地吃上一顿儿媳们给他准备的可口饭,然后抽上一根饭后烟,便要回去准时午休了。如果发现有啥可以带的好吃的东西,他会说,这个我带点给你妈吃,然后就牵出他的自行车,“蹬蹬”两下熟练地上了车,载着他那满满的幸福感,消失在街道的那一头。父亲那人车远去的背影,至今我依旧历历在目,很暖心,很不舍。
那时候,我已经在隔壁乡的镇政府工作了,几天才回家一次,每当我回到家,便会合计和家人一起,傍晚时分,带上几样菜回到老家,去和父母一起晚餐,享受母亲做的饭菜,跟父亲喝上几杯小酒,然后父子们泡茶聊天,整个院落里充满着欢快嘈杂的谈笑声,常常惊动五邻四舍,翘起耳朵偷听。父亲见到我们回家,那个高兴样写在脸上。有时遇到他不在家时,母亲便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出去找人,她知道父亲会去那里,果然不一会儿父亲便会回来。我晓得,无论外面有多重要的人在,或是有多重要的事情在商量,只要一听说子女们回来,父亲定会放下他们立马回家,然后便泡茶、抽烟、聊天、吃饭。这种无以类比的人生盛宴,是我记忆中最快活的事情,如今已成为奢望,万求不复!
1995年的秋天,一天早上,我在家刚吃完早饭,忽然父亲来了,他边走进门来右手边摸着肚子说这几天这里有点不舒服,我即刻说今天刚好我在家,稍后带你去卫生院检查,没想到这次他一下子就答应我说好。记得以前一说到医院看医生,父亲都非常的排斥。乡卫生院就在镇区,我们很快就来到卫生院,上楼找了一个本地的姓黄的医生,他简单的问诊后,建议做B超检查,等我拿回片子给黄医生看时,他只是眼睛扫了一下片子,就说“好好,你带你父亲下楼休息会,稍后来拿片子”。我当时哪想到问题有多严重,待我再次上楼,黄医生就举高片子对我说:“已经是9*11了,肝CA晚期了,我开点药回去吃,有好东西多买些给他吃,顶多四个月的”。我一下子脑子如五雷轰顶,鼻子好酸,眼睛一下子湿润起来。太突然了,怎么可能呢?出来后,我走到二楼走廊的尽头,面对窗外,眼泪还是不停留。过了一会,待我平复心情后,就下楼来,眼睛不敢正视坐在走廊边长椅上的父亲,只是对他说:“医生说是肝有点问题,吃吃药就好的。”父亲应了一声:“有问题也没办法。”我随后到药房排队抓了药后,就带父亲回到家中。那天晚上,我急忙通知在家的老大、老三、老四回来商量,又给当时已在美国洛杉矶工作的五弟打了越洋电话,大家拿出一个治疗方案,同时形成共识,除兄弟“五大常委”外,对任何人不得告知父亲真实病情!接下来的那段日子,便是省内外四处求医,力求最佳办法挽留住父亲,能多活一天算一天。
是老天爷的挽留抑或是子女们的孝心感动上帝,本来说只能再活四个月的父亲竟然就是一个健康人一样再活了五年还八个月。在这期间,他由五弟陪着去游玩了北京的故宫长城,还去登了泰山,玩转了孔庙孔林等省内外多个地方。也是在这期间,他亲历了老大、老二仕途升迁,老三、老四、老五事业发展的过程,亲自操办了七妹、八妹、九妹婚庆喜事,主持子女们奋发图强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
新居乔迁、事业庆典等重要仪式,饱享因此而带来的一波波特大的喜悦。他还如往年一样,每逢大年三十围炉,他和母亲总是服装整齐地坐在酒桌的大位上,酒过三巡之后,总结着家族每一个小家庭一年来的诸多喜事,给孙辈们发红包,也接受着儿孙辈们给他发的红包。所有这些,历历在目,仿若昨日。即使是后期8个月他开始需要儿女昼夜陪护期间,他也基本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几无疼痛,能吃能睡。
但这一天终究来到了,2001年春节过后的一天,父亲经受了两个昼夜的不停打嗝终于体力不支卧床不起了,直至这个时候,他看到儿女媳妇们每天陪护床边的情景时,才顿然悟到,五年来家人瞒着他说是肝有点问题需要定期检查、长期治疗的说法,并非那么简单!他知道大限将至,等到有一次我们在家兄弟都回老家去看望他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只喝了半碗汤,要大哥扶着他半坐着倚在床头,他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翻身都要依靠别人搀扶了。他声音细弱地问我:“外面还有谁在?”我回答他说都在这里了,他“嗯”了一声,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们,说:“我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了,人走是正常的,后事要新式来办,要给我穿西装……不能停留太多天,饭菜要让人家吃好……”然后又抬了抬头望着站在房门口的母亲说:“你跟着我吃得苦不少,现在命好了,不用消极……这些年借给别人的一些钱,有拿来还得来还,没有来还的就不要去问了……”父亲讲这些时,神情淡定,丝毫没有一丁点对生的依恋和对死的恐惧,倒宛如平日一般在谈别人家的事情一样。在场的大妹、二妹忍不住哭出声来,父亲还让她们不哭。看到父亲如此豁然,我心里倒也宽慰许多,默默记下了父亲的话,这也许是父亲在这个世上要表达的最后一个人生态度了。
父亲终究还是走了,那是在他交代完后事的第四天晚上,我站在床前,久久端详着他那没有半点牵挂和遗憾的安详的脸,用手轻轻地捋着他那花白的头发,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滴,心底里涌动着无限的酸痛和不舍。父亲,是您给予我生命,给予我们一口口饭吃,给予我们走好人生路上的一次次叮咛!多少年来,我无数次地想,您如果能活到80岁该多好啊,您就可以在这些年中多抽很多很多好烟;就可以在几年前的那次我们四兄弟陪母亲出游,纵横六省,历程一万里路,玩遍祖国名山大川时,能多上您老,一同感受母亲激动不已的心情;就可以继续大年三十家族围炉大会,一次次聆听您的年终总结,分享您收受红包的跨年喜悦……
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曾经无数次我在梦里见到您,可您却不等我醒来就走了。如今的我,只能在每次的思念中道一声:父亲,我永远想你!
二〇一八年一月六日
如果觉得《父亲——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正阳(作者:亦青子)》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