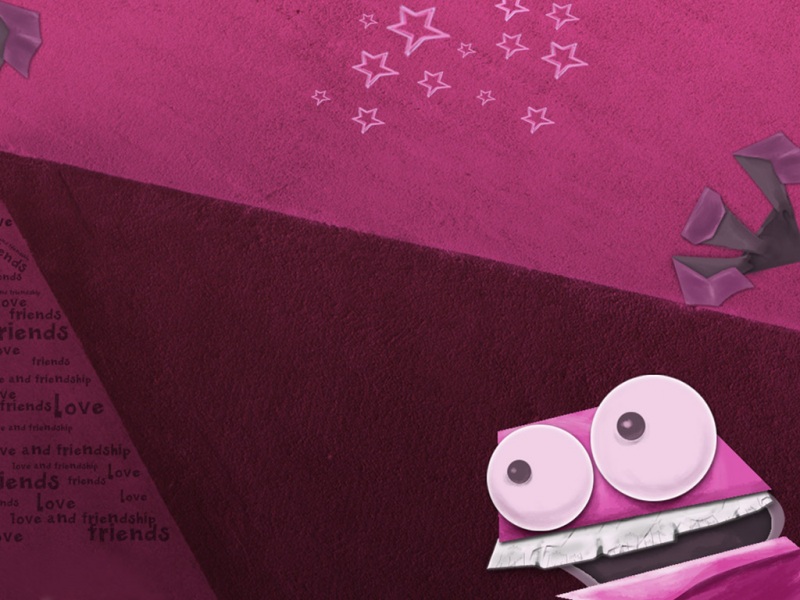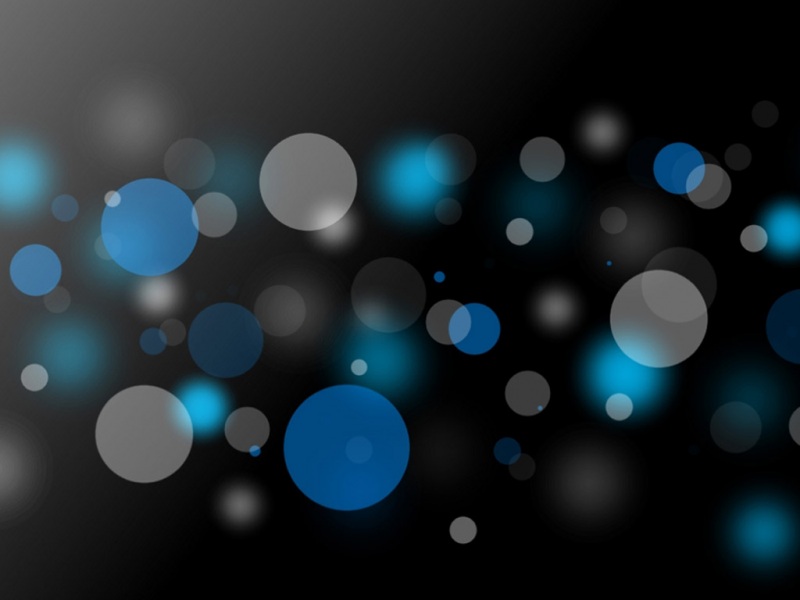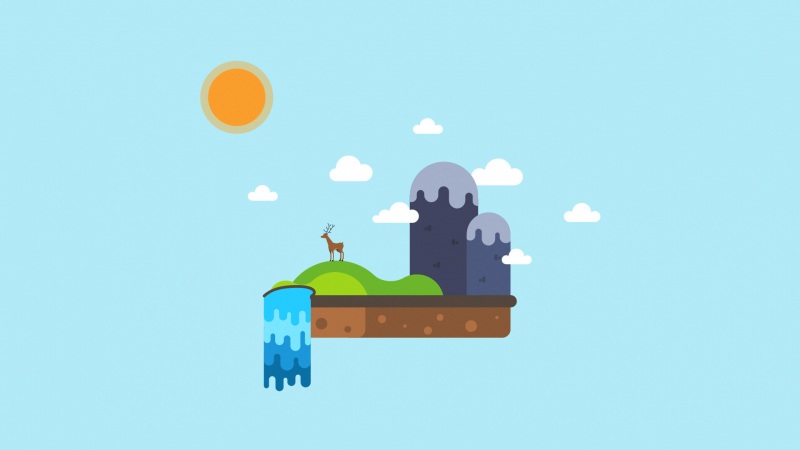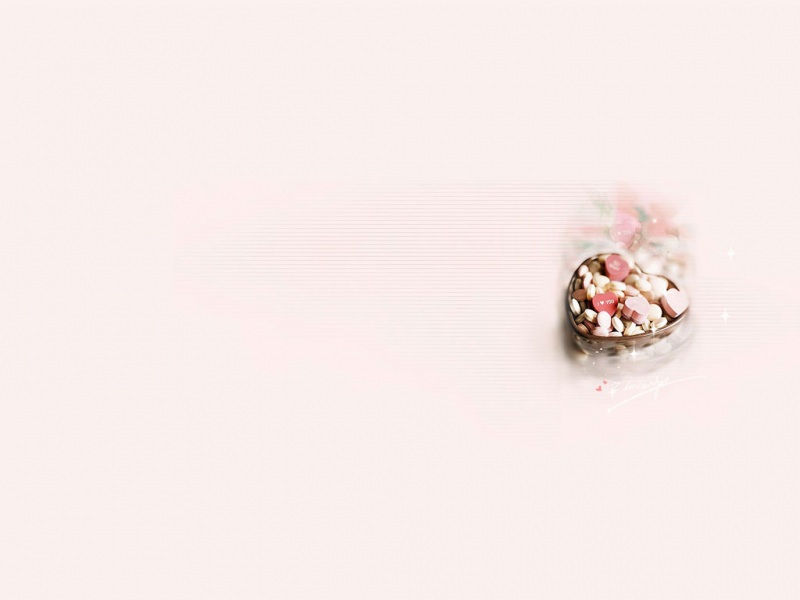曹魏景元元年的一个深秋,子规急于回巢,嘤嘤着掠过树梢,沧州之上升腾起一面隐约的雾气,晚归的农人赶了牛车嘎吱着走向山脚。
山林中的夜幕刚落,林荫下的一间茅屋中,一曲《风入松》已起了调。数百载间,这片山林之外的世界不断地发生着沧海横流,八方风雨,斗转星移的重大事件。
而一群好琴、好酒、好思辨的人正隐匿在这山涧之间,他们一面“临清流,赋新诗”,一面“背长林,翳华芝”,像仙人,又像流亡者,过得好生快活,却又好生地不快活。
一曲终了,余音靡靡。朗月垂光,映照出他们高深莫测的面庞。天晓得,这座山是什么山?这片林是哪个林?这群人是何许人?
推杯换盏之间,远处的林间似有野兽跳跃而出,尾似长鞭,角如梅枝,毛同锦缎,眼如珠玉。屋里传来酒杯碰地的声音,一人喊道,快看,那是山泽瑞兽!众人拾了鞋奔出门外——湿润的山间只余麋鹿的蹄印,却已不见它的身影。
1. 逃亡的文人:从一个失乐园,到另一个失乐园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至公元260年左右,曹魏方面有司马家族权倾朝野,东吴有权臣凶虐、孙亮被废,蜀汉余了一名“扶不起的阿斗”,胜败局面已呼之欲出。
公元266年,司马炎结束了与曹氏家族之间的拉扯,正式篡魏,西晋如同一声惊雷般迅速崛起,并在公元280年灭吴后一举结束八十余年的乱世局面,实现了自秦始皇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一统。
然而,西晋的统一却与秦王朝的一乎天下截然不同。秦王朝开启了持续四百多年的礼教、经济与文化方面的统一。而西晋却打开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潘多拉之盒:在接下来的三百六十余年间,共计三十余个王朝相继兴灭,并发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重要历史事件。
政权的反复更迭及战乱带来紊乱的经济发展,贫苦农民向士族及寺庙卖出土地以求生存,而大地主、贵族和官僚却纵情享乐、攀比财富。
与此同时,民族融合加强,佛教、希腊以及波斯文化传入中原,带来经济形式、生活方式以及思想上的冲突和改变。中原大地呈现出一派星飞云散、颠沛流离的混沌景象。
存在于这一段时期的文人是悲惨而郁结的。政治形势风云突变、波谲云诡。在王公贵族之中,政变成为一种流行的手段,而在士大夫及文人之间,“站队”和“说话”则成为两门艰苦的学问。
文人的立场如风中浮萍,飘摇不定:在更迭的朝代里,大量名士包括谢灵运、崔浩等人被构陷,身家陨;在新建立的王国中,选官制度趋向于任人唯亲,身世背景成为唯一的依据——可谁又能知道国家下一次姓什么?
王朝更迭之间,文人不断地从一个失乐园进入到另一个失乐园。“齐家”保命竟须步步惊心,“治国”安民显然遥遥无门,天下正乌烟瘴气地乱着呢,更不要说“平天下”。
几经铩羽,牛马风尘,现实的围城给了形而上的思想可乘之机,悲观的避世倾向开始在文人之间蔓延乃至流行。
2. 青山四处埋尸骨,我登鹿门永不还
世上曾有多少次天崩地裂的动乱和金尽裘敝的失意,便有多少份想要埋头逃避、远走高飞的心情。隐居作为一种社会性选择,在中国古代其实早已存在。
古代文人大多得意时仕,失意时隐,印证的是孔子所提出的“邦无道则隐”;后又有庄子形而上的“心隐”,东方朔“大隐隐于市”的“朝隐”;
乃至白居易提出“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伯夷叔齐因耻食周粟而隐居首阳乃至饿死,是一种坚定的明志;
林逋一生不仕不娶,结庐孤山,与梅妻鹤子为伍,是为骨子里的孤傲与清高庞德公携妻女上鹿门山后从此采药不返,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想要避开俗世,隐居于某处,其实是常见的人类心态和社会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上升为一种浓郁的风气。
在前后近四百年中,出现了诸多著名的隐士,他们各自因为所处的时期、政治环境、家庭背景及个性差异,体现出各不相同的隐逸风格。若要就他们的隐逸事迹做个粗浅的分门别类,那么大致能够分为四种。
第一种隐士为说隐就隐,楚河汉界,态度分明。这类人物以嵇康为代表,蔑视礼教,崇尚自然,与当政者势同水火,对于当下的潮流和世俗有着深刻的不屑一顾。
嵇康原本忠于曹魏政权,隐逸也是自司马家族篡位后开始。在整个魏晋南北朝的隐士当中,嵇康的才情才艺、狂放不羁、社会声望乃至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均有着一骑绝尘的实力。
李叹其文章“峻绝可畏”,刘赞其品性“清峻”、是为“隽侠”,白居易写诗为其“涕泪满裳”,冯友兰评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
嵇康之所以受到文人广泛的喜爱,正是因为其刚肠疾恶,爱憎分明的果敢和骨气,以及他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浩然的思想立场。
然而,这样的个性遇贤则矣,遇佞则溺。在得知好友山涛好意将自己举荐给司马朝廷时,嵇康勃然大怒,奋笔疾书,怒写长篇巨制《与山巨源绝交书》。
文章酣畅淋漓,脉络分明,有理有据,逻辑严密,毫不遮掩地向挚友山涛流露出指责、尖刻与傲慢,然而贤者山涛终以宽宏待之。
而在面对因仰慕而前来拜访的钟会时,嵇康因认定来者为俗人,怠慢钟会,甚至抛出轻蔑的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后来,钟会向司马进谗言称嵇康为“卧龙”,嵇康终究给自己埋下殒身的祸根。“营内而忘外”是嵇康的特点之一。
他不喜俗人,又不肯憋着,必须言明立场,道清身份,叫这些人看清自己的愚蠢,这在招致大量仰慕者的同时,也广树外敌。在旁人看来,他的言行就有了“名重伤身”、“不合时宜”的过失。
魏晋隐士的第二类型为半隐不隐型,主要以阮籍、山涛和刘伶为代表。山涛和阮籍都是嵇康的至交。
在断袖之气蔚然成风的年代,三人的关系曾好到让山涛的妻子心生怀疑。山涛幼时孤苦清贫,因此在被司马师举为秀才后,至此格外珍惜仕途,始终恪守本份、选贤用能。
山涛虽然不似嵇康那般恃才放旷、旗帜分明,但他为人正派,品格高贵,度量恢弘,“璞玉浑金”。
虽然在职期间屡求退位,希望归隐田野,仍因风德高尚、治理有方,屡次辞官不成。山涛与嵇康之间即使有绝交书事件存在。
但他仍是嵇康死前唯一的托孤对象,二人在志趣和理想上,实则有着莫逆于心的交情。阮籍在为人上比嵇康更为圆滑。很少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嵇康赞其“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只有“饮酒过差”是他的缺点。阮籍和刘伶都是酒鬼。
阮籍为了步兵校尉府中的美酒接下校尉的官职,实则每日偷闲躲静,一遇正经事就装醉。刘伶对于酒的痴迷更甚,常常鹿拉轻车,纵酒昏酣,后又特意作了《酒德颂》,用来隐射现实。
在嵇康下狱、阮籍病死后不久,太康时代终于到来,社会呈现出一片安宁繁荣的景象,竹林七贤中的向秀、王戎、阮咸等人再次积极地寻求入仕。
他们体现的则是第三种隐逸:能隐则隐,不隐则矣;隐无可隐,无需再隐。换句话说,当形势明朗,机会出现,他们仍愿投身朝廷,实现治国志气。
西晋虽是一个伟大的朝代,但伟大的人物却在其之中变得平庸。曾经雄才大略、明达善谋的司马炎开始追求别出心裁的放纵。
西晋的没落弹指之间,仅二世而亡。晋人为躲避匈奴人的进攻,举家南下,开辟了东晋。正是在嵇康与阮籍去世一个世纪之后,陶渊明诞生了。
陶渊明代表着第四种隐逸,即,隐便隐了,无需再提。隐士如陶渊明、庞德公等在内,均体现了坚定的志气,但一旦归隐,就索性连意见也懒得发表。
文人的作品能够体现出其心境,陶渊明的诗作开辟了田园诗、隐逸诗的新篇章,清新明朗,悠闲快活,体现了真实的平淡和释然。
相较于陶渊明,嵇康归隐后的论作仍彰显着他犀利的笔锋,孔武有力的论辩和强悍的个人态度,这或许还意味着怨恨,意味着不甘。
3. 阵痛下的新生:建给后世的复乐园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上的无序通常为新事物的探索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政治上的动荡和混沌必然带来文化与思想上的遍地开花、百家争鸣。
一方面,秦汉一统的瓦解松动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权威,“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消耗着社会对这一学派的信赖,使得道家、法家、佛家等思想能够趁虚而入,寻得一方立足之地。
另一方面,身处混沌之中的文人在折磨中生出了对虚无的渴望和好奇,以形而上的道家思想为基础的魏晋玄学应运而生。
深奥的玄学对本我,他人,自然,以及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了真挚的探索,在混沌的当时给人们带去了慰藉心灵、振奋精神的作用,同时对后来的中华哲学乃至世界哲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而在文化审美方面,这一时期的诗词造诣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演变和升华。在诗歌风格上,隐逸诗和山水田园诗避开了严酷的现实。主张片段化、场景化的自然景观描写,凸显闲适自然、宁静娴雅、质朴清新的诗歌意境,继而寓情于景,传递深意。
在美学意象和行文方式上,严酷的政治环境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言论自由的可能性,隐士对于感官及意气的表达倾向于曲折和隐晦,因此出现了隐喻、比兴、象征等手法。
除了麋鹿、沧洲、五柳、鸥鹭、东皋、牧童、子规等大量的特指隐居山林的意象之外,隐士及文人还常常用到以物代人的手法。
例如,嵇康在自己的《琴赋》中提到,“然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郄;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
全篇虽在刻画琴之态、琴之美,实则却在表达自己交友的原则和旷达的心声。
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低调的反世俗反而变成了高调的非主流,有时隐士们隐晦的自我表达在外人看来,就有了阴阳怪气、含沙射影的意味。
后记:二十一世纪,隐逸文化是否可取?
隐逸文化在中国历史、文艺以及哲学发展领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当人类进入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社会管理极为先进的现代社会后,隐居变得困难。
甚至不再为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在现代化国家当中,似乎只有日本与芬兰还保留甚至继续发扬着离群远居的社会文化。
而原因大多仍是为了逃避社会现实、确保必要的社交距离、断绝累赘的社会关系。
然而,我们所立足的空间本就充满了动机、关系、责任与感情,充斥着喜悦、悲伤、恐惧、挫败与灰心,以及无数个与我们感情相似的其他人,这才是真正的世界。
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还能心无旁骛地抛下一切去隐居吗?就现状来看,或许只有新冠病毒做到了。
了解历史使我们明白了历史人物所面临的混沌意味着什么,而他们又于其中挣扎着创造出了什么。如果于混沌之中抽身远离即意味着获得了新的视野和立场,隐居是否也可被视作为一种生活的创意?
可是,真的可以仅因恐惧和失落就离群索居吗?
抹除了恐惧不意味着增加了勇敢,行动之阻助长行动,道路之阻自成道路,恐惧者和失落者需要知道的不是这个世界有多可怕、多令人灰心,而是明白他们自己可以变得更强大。
直面现实的勇敢意味着像狩猎者一般保持警觉,并始终尝试使自己有能力应对危险和未知。但若要隐去,便是真的一去不返。回想一下你的人生,你真的想好了吗?
参考文献:
《汉晋春秋》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
《琴赋》
《与山巨源绝交书》
文/羽昕
如果觉得《魏晋南北朝时期 文人隐逸的风气:从一个失乐园 到另一个失乐园》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