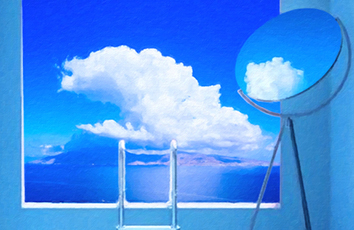意识和潜意识.支离破碎(1)
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是意识和潜意识,浮面的心和深层的意识。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生活分解得支离破碎?例如,上班生活、社交生活、家庭生活、宗教生活。为什么不但我们自己,连社会生活上都有这种分别—我们和他们、你和我、爱和恨、死和活?我认为我们应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种完全没有生死、意识与潜意识、上班生活与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区分的生活方式。国家、宗教、阶级的分别,个人之间一切矛盾的分别,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这种生活带来了动乱、冲突、战争,带来了真正的不安,从表象到本质都是这样。种种的分别—上帝与魔鬼、恶与善、“实然”与“应然”实在是太多了。我想用今晚的时间来寻找一种值得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是理论和知识,而是没有任何分别的生活,它不会导致支离破碎的行为,而是持续不断的流。在这个流中,每个行为都和其他行为有关。
要寻找这种不支离破碎的生活方式,必须深入探讨爱与死的问题;明白我们可能找到一种生活方式是持续不坠的动,不破碎。这是一种高度明智的生活方式。支离破碎的心缺乏的就是明智。过着“半吊子”生活的人,大家认为高度道德的人,显然缺乏的就是这种明智。对我而言,“完整”就是拼合所有片段而形成一个整体的观念并不明智,因为这个观念另外蕴含一个“整合者”的意思。这个整合者整合、拼凑所有的片段。然而要做这种事,实体的本身就是一个片段。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明智与热情,从而创造个人生活的根本革命,使行为不再矛盾,而是完整持续的动。要创造这种生活的变化必须有热情。我们只要想做什么有价值的事,都必须先有高度热情—这种热情不是快乐。要了解一种不支离破碎,没有矛盾的行为,也要有这种热情。知识的概念和方式改变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改变生活方式只有先了解“实然”,要了解实然就先要勇猛,要热情。
我们必须先了解快乐的本质,才能找到一种生活方式。这里不是指修道生活,而是日常生活方式。然后,拥有这种热情与明智。前几天我们讨论过快乐的问题,讨论过思想如何延续为经验,经验使我们拥有一瞬间的快乐。我们讨论过因为想到快乐而使快乐延续。快乐之所在,必受限于痛苦与恐惧。爱是快乐吗?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依据快乐建立道德观。牺牲自己、克制自己以与他人苟同,皆为追求快乐,也就是想要伟大、高贵。爱是快乐吗?我们现在看到的又是一个负担过重的字眼。我们每个人,从政治家到夫妻,都在用“爱”这个字。在我而言,就爱最深刻的意义来说,只有爱才能带来一种毫不支离破碎的生活方式。恐惧是快乐的一部分。显然,关系中只要存在恐惧,不论这种恐惧是什么,必然支离破碎,必然分裂。这真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人心为什么总是分裂而与他人对立并由此造成暴力,企图由暴力达到某种东西?人类的生活方式导致战争,可是却又向往和平,向往自由。这和平只是个概念,一种意识形态。我们所做的一切统统都在制约自己。
人心有种种“分裂”。譬如在心理上分裂时间。时间在我们心里分裂成过去(昨天)、今天、明天。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一种没有分裂的生活方式,就必须努力探索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思考,时间也就是分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心理时间,是否是这种分裂的原因?分裂是不是由成为过去的记忆和大脑内容的已知事物所造成的?或者之所以分裂,是因为“观察者、经验者、想的人”总是与观察、经验的事物互相隔离所致?或者之所以分裂,是因为种种自我中心的行为,所谓的“你或我”制造了自己的孤立行为、抗拒?“观察者”与被观察的事物有所隔离、经验者与经验有别、快乐,这一切是否与爱有关?
诸如此类,若想探讨分裂,必须先清楚是不是真有心理上的明天。真正的心理明天,不是由思想发明的吗?年鉴时间确实有明天,但是心理上,内心里是否真有明天?观念上有明天,行为就不完整,这个不完整的行为就造成分裂与矛盾。“明天、未来”等观念能不能使我们看清楚事物目前的状况?“我希望明天再看清一点。”我们很懒。我们没有热情,缺乏高度的关切去弄清问题。思想发明了“终将到来、终将了解”的概念。这一来时间就成为必要,太多的日子就成为必要。时间会使我们了解事物,看事物很清楚吗?
我们的心可以没有过去,因而不受时间约束吗?明天在心理上属于已知,那么心有没有可能免除已知?行为有没有可能不属于已知?最难的事是沟通。口头的沟通显然必要,但我想还有一种深层沟通。这种深层沟通不仅是口头沟通,而且还相投。这是因为沟通双方属于相同的层次,同样的密度,同样的热情。这种相投比纯粹口头的沟通重要多了。如果我们讲的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一种深深触及日常生活的东西,那么这其中必然不只是口头沟通,而且还相投。我们关切心理上根本的革命,不是多久以后的革命,而是今天,现在的革命。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心饱受制约之后是否可能立即改变,因而使它的行为恢复为连续的整体,不支离破碎;因而消弭它的悔恨、绝望、痛苦、恐惧、焦虑、罪恶感。心如何抛除这一切而变得全新、年轻和纯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认为,只要我们的心仍处在分裂成“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分裂成经验与经验者,这种根本的革命就不可能。这种分裂造成了冲突。所有的分裂都必然造成冲突。冲突、斗争、战斗虽然可能造成一些粗浅的改变,可是在深层心理上绝不可能造成任何改变。所以,心的整体状态如何处理分裂问题?
我们说要讨论意识和深层的潜意识。我们问为什么有分裂:一方面是意识心(其中充满了日常行为、烦恼、问题、浅薄的快乐、谋生),另一方面是深层潜意识心(其中隐藏着种种动机、欲望、要求、恐惧)。为什么会有这种分裂?这种分裂的存在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浅薄的喋喋不休,一直在宗教和其他方面欲求浅薄的惊喜、消遣?我们这浅薄的心,在有这种分裂时根本无法深入发掘自己。深层的心有什么内容?我们不要依照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的看法,如果你未曾听别人怎么说,你要如何去发现?你如何寻找你的潜意识是什么?你会不会注意你的潜意识?你是否期望你的梦能解释潜意识?专家呢?他们照样受到自己“专门化”的制约。
也有人说,可不可能完全没有梦?当然,除了吃错东西,吃太多肉所以做噩梦之外,潜意识(我们暂时用这个字眼)是有的。潜意识是怎么形成的?显然是过去的种种,一切种族意识、种族残余、家族传统、宗教社会制约—隐藏的,晦暗的,未发现的。如果没有梦或者不去找精神分析医生,这一切是否可能暴露?没有梦,心确实睡着了,就很安静,不再一直活动。如果心安静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质素,一种与日常焦虑、恐惧、烦恼、问题、欲求完全无关的质素是否能不再进入心里?要解答和发现这一点,是否可能?也就是,因为完全没有梦,所以心早上醒来完全新鲜,我们必须在白天就很留心,留心种种线索、踪迹。这一切只能在种种关系中发现。你观看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没有怨恨、判断、评价;你观看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反应,只是看而没有任何选择。这样,所有隐藏的潜意识,在白天亦将暴露。
我们为什么赋予潜意识这么深刻的意义?潜意识和意识毕竟一样无足轻重。如果意识心异常活跃,一直在观、听、看,那么意识心就比潜意识重要得多。在这种情形下,潜意识的一切内容将完全暴露,各层次间的分裂也将终止。坐公车时,跟自己的太太、先生谈话时,在办公时,写字时,孤独时(如果你曾孤独,看看自己的反应)。那么这整个观察的过程,这个看的行动(这其中没有“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分别)将使矛盾停止。如果这一点多少清楚了,我们就要问:爱是什么?爱是快乐吗?是嫉妒吗?占有吗?爱是丈夫支配妻子、妻子支配先生吗?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爱。可是我们身上却背负了这一切,然后告诉我们的先生太太或什么人,“我爱你。”再者,我们大部分人,不论是这样的嫉妒或那样的嫉妒,总是嫉妒别人。嫉妒来自于比较、衡量;来自于希望不同于现状。那么,我们是否可能实然的看见嫉妒,因而永远不再嫉妒和完全免于嫉妒?如果不能,爱就永远不存在。爱,与时间无关;爱,不能耕耘;爱,与快乐无关。
再者,死是什么?爱与死之间的关系如何?我想,只要了解死的意义,我们就会发现两者的关系。要了解死,显然必须了解生。这个生是日常生活的生,不是意识形态的知识的“生”。我们以为这种生应该就是生,但其实是假的生。我们的生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生就是日常冲突、绝望、寂寞、孤独的生。我们的生活,不论睡或醒都是一个战场。我们利用各种方式,借着音乐、艺术、博物馆、宗教或哲学的排遣、构筑理论、沉浸于知识等,企图结束这种冲突,封闭这个一直给我们悲伤,我们称之为生活的战场。生活的悲伤可能结束吗?我们的心若不根本改变,生活就没什么意义。每天上班,谋生,看几本书,也能聪明地引用别人的话,资讯也变得充分,可这是空虚的中产阶级的生活。
然后如果有人发现这种情形,他就开始发明一种生活意义来给生活,他会去找聪明的人来给他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这又是另一种逃避。这种生活必须做根本的转变。我们大部分人都怕死。为什么我们都怕死?我们究竟怕什么?请看看你称之为死亡的那种恐惧—你害怕抵达那个称之为生活战场的终点。我们害伯未知,害怕可能发生什么事。我们害怕离开已知的事物:家庭、书、住宅、家具、身边的人。可是这已知的事物是悲伤、痛苦、绝望,偶尔有些快乐。这不断的挣扎永无休止,我们称之为生活,可是却害怕放手。害怕这一切会结束的,不就是这一切累积出来的“我”?
所以“我”需要未来的希望、需要转世。整个东方都相信转世。转世就是说你下辈子会爬得比这辈子高。这辈子你是洗碗工,下辈子就是王子。至于洗碗,另外有人会替你洗。相信转世的人这辈子对他很重要。因为你的下辈子都要看这辈子的所作所为与思想、行动而定。你不是得好报,也不是得恶报。但事实上,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行为如何。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信仰,一如相信天堂、上帝,随便你喜欢。事实上,真正要紧的是你现在、今天怎样,是现在、今天的所作所为;不但外在,而且包括内在。至于西方人也有他们安慰死亡的方法,西方人将死亡合理化。他们有他们宗教的制约。
第2节 支离破碎(2)
所以到底死是什么,是结束吗?有机体会结束,因为有机体会老,会生病或发生意外。我们很少有人老了还很漂亮,因为我们都是受苦的身体。我们一老,脸上就显示出来。另外,老了还有回忆的悲伤。我们可能心理上每天都免于一切“已知”吗?除非有免于“已知”事物的自由,否则永远掌握不到那“可能的”事物。本来,我们的“可能性”一直都局限在已知事物的领域内,可是一旦有这种自由,我们的可能性就广大无垠。所以可不可能在心理上免除过去,免除一切执著、恐惧、焦虑、虚荣、骄傲?完全免除这一切,所以隔天醒来成为新鲜的人?
你会说“这怎么做?有什么方法?”这没什么方法,因为“方法”意味着明天,意味着你要不断改正。最后,明天,很多明天之后,终于改正为某种东西。但你是否现在就能看清一个真相——实际的看,不是理论的看?这个真相就是,除非心理上终止过去的一切,否则我们的心不可能新鲜、纯真、年轻、有活力、热情。但是我们不愿意放弃过去的一切,因为我们就是过去的一切。我们所有的思想以过去为基础。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过去,所以我们的心放不掉。不论它做过什么努力想要放弃,这努力仍是过去(希望成就另一种状况的过去)的一部分。
心必须非常安静。而且只要心里清楚整个问题,就会非常安静,没有抗拒,没有任何体系。人一直在追求不朽。他画画,签个名,那就是追求不朽的方法。人总想留下自己的什么东西,所以留下他的名字。他必须给的,除了技术性知识之外,还有什么能给呢?心理上他是什么?你和我,我们是什么?你银行的存款可能比我多,可能比我聪明,可能比我这样或那样;可是心理上,我们是什么?一大堆话、记忆、经验以及我们想传诸子孙、写成书、画成画的一切,以及“我”。这个“我”极为重要。这个“我”与社群对立;这个“我”,要认同自己;要实现自己;要成为某种伟大的人、事,你们知道,想要成为所有的一切。你观察这个“我”,看见一大捆记忆和空洞的话,我们执著的就是这些。这就是你和我之间,他们和我们之间那种隔离的本质。
如果你了解这一切,不经由别人而是经由自己,不判断,不评价,不压抑,只是观察,仔细的看,你就会知道,只有死,才可能有爱。爱不是记忆和快乐。据说爱和性有关,这又回到欲爱和圣爱:取其一,则另一就分裂。当然,这些都不是爱。除非告别过去的一切,告别一切劳苦、冲突、悲伤,我们不可能完全而整体的触及爱。告别过去的一切,然后才有爱,然后才能随心所欲。前几天我们说过,问问题很容易;但是问得有目标,时时谨记在心,一直到自己完全解答问题则不然。这样的问有一种重要性,随意的问则没什么意义。
探索心智
如果说我要探索心智的问题,就是说“我”要探索我的心智:为什么它受到控制,它受到多么深刻的控制,它能够从控制中完全解放出来吗?只有解放了心智我才可以和其他人建立正确的关系,否则我深受控制的心智就会让我支离破碎,就会在你我之间制造分裂。我关于“我”的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东西,所以我首先要找到谁是那个探索者。支离破碎的“我”其中一个碎片正在探索——一个碎片,一部分“我”说,“我要探索其他部分”,哪一部分是那个受到控制的“我”呢?一个碎片假装它有能力、有权威去探索其他碎片。一个碎片继续把其他碎片打成碎片。如果一个碎片假装它可以探索其他碎片,那还是探索吗?
那不是探索。它只是把“我要探索”当成了一个结论。你明白了吗?它只是一个结论,结论继续带来分裂。探索必须没有结论,没有假设。假设的意思是立论的基础,如果你从一个基础开始,你不可避免地会得到一个结论,你背负着这个结论来探索,这就制造了分裂,所以这样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探索。如果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能够走得更远。
我正在探索的心智,已经没有预设结论了吗?就是已经没有“我要探索”这个结论了吗?一个结论就是表达一个愿望,对吗?当我说“我将探索我自己”,这是一个结论,表达了我希望理解、希望超越的愿望,表达了我希望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目前的苦难将在那里不复存在。所以说,它是一个结论。它是一个愿望的表白,“我要探索”。我的心智可以从这个结论中解放出来吗?否则,我就不能探索。就像一个科学家:如果他想要探索,他开始寻找,但是他不会从一个结论出发——如果是那样,他就不是一个科学家,他只不过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了!
所以探索、探询,必须没有预设结论。只有这样,心智才清新、清澈。这样,当你探索的时候,还有探索者吗?这样只有观察,没有探索。因此你的心智不会支离破碎,只有不分裂的心智才可以观察。观察的意思是,没有预设结论的洞察力,并且因此而洞悉一切。你听懂我说的这些了吗?这样你的心智完全自由,你可以自由地观察,你可以完整地、自由地行动。
提问者:心智怎样才能不受限制,怎样才能不机械?
克里希那穆提:我们的心智是一台小小的受到控制的自动机器。你问,我怎么才能从中解放出来?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不过好吧,让我们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的心智是卑微的、渺小的、机械性的——我该拿它怎么办?你知道你的心智是渺小、卑微、焦虑、羡慕、嫉妒、争强好胜、总是和人家攀比?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心智就是这个样子吗?噢,看在老天的份上,让我们诚实一点吧!好了,我知道我是这个样子的。我该怎么办呢?
当你说“我明白这个”,你所说的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当你说“我知道这个”,你所说的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请注意,这很重要。你知道你的心智是卑微的,是不是因为你把它和其他不卑微的心智进行了比较?我说“我的心智是卑微的、狭隘的、愚蠢的、迟钝的、白痴一样的、神经病的”,我怎么知道这个呢?因为别人对我这样说的?因为我把我的心智和另外一个我认为不像神经病的、我认为是自由的心智进行了比较?因为比较,我发现了我的卑微;因为衡量,我发现了我的神经病?因为比较和衡量,我们才变得卑微。我不知道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洞察,你明白了吗?我衡量自己,我把自己和你比较,你是这么聪明、充满阳光、目光如炬、美丽漂亮,于是我说:“噢,老天,我是如此丑陋!”
这是什么意思?我在比较里面发现了我的丑陋。我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教育要我总是把自己和别人比较——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在我成长的每一步——总是用他人来衡量自己。所以我对自己说,为什么我总是比来比去的?如果我不比较了,我还是丑陋的吗?我不知道。我认为比较让我丑陋。请你跟上我所说的。这是一个洞察。有史以来我们受的教育让我们比较,从宗教的、经济的、社会的,从每个方面来比较、来衡量——比较衡量可以结束了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当我洞悉了它们的愚蠢,比较衡量就结束了。
我为什么要拿自己和你比呢?你也许是这世界上最非凡的人物、最伟大的圣人,你也许是救世主,但是我为什么要拿自己和你比呢?因为我所受的教育要求我这样做——我的哥哥比我好,我的叔叔比我聪明多了。现在我有了洞察力,它说,不要比较了,那是愚蠢的。因为我有洞察力,我停止比较。现在我是什么呢?你跟上了吗?我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跟上我了吗?当你不把自己和他人比较的时候,你是什么?
你会自己找到答案,是吗?你不再说“我是卑微的、渺小的、平庸的、狭隘的,我是多么丑陋”。我在比较中得出结论,结论会扼杀洞察力。我有洞察力,它让我看到比较是多么愚蠢。我不再比较了。比较结束了,永远结束了。因此我将看到真正的自己。当我拒绝比较的那一刻,我就不再愚蠢了,因为我已经看清楚比较的整个结构了,这就是智慧。比较可以得出卑微或者伟大,无论卑微或者伟大都是相对的,而智慧是超越所有相对性的。你听懂了吗?
意识和脑细胞
普:让我们来讨论意识和脑细胞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不是具有相同的性质?有没有一个东西赋予它们不同的性质?
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由你开始吧。
普:在传统概念里,“意识”这两个字包含了超越思考及经验范围之外的东西。
阿:没错。脑子只是一群细胞的集合体。虽然细胞和细胞之间互相依靠,但是每一个脑细胞都能独立运作。现在我们就来想一想要如何了解这些意识的集合体,也就是所有脑细胞的统合?有没有一个统合的因子存在?脑子是否只是它的果?接着我们又要问了,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是先有意识再有脑子?还是先有脑子才有意识?
克:我可不可以问你,你所谓的“意识”是什么?让我们从头开始。什么是意识?“觉察”又是什么意思?譬如找眼前的这个麦克风,我先觉察它的存在,然后才想起来用“麦克风”这三个字。因此当你觉察某样东西时,你就立刻给它一个名称,然后好恶就产生了。因此“意识”包含了觉察、觉知、感觉、认识和接触。
阿:我认为意识在感觉之先。在任何时刻我通过感官都只能察觉意识的一部分。我觉得意识要比感觉广大得多。那个浩瀚的领域并不在我的觉察之内,因此我不能说每时每刻都能完全觉察我的意识。
克:那么意识和脑细胞之间有什么关系?
普:克说所有的觉知就是意识,似乎意味着脑细胞也是意识。如果在脑细胞之外还有意识的领域,那么你就不能说所有的觉知就是意识了。
克:这点清楚了没有?我曾经说过,所有的觉知就是意识。
阿:这句话和觉知者无关。这句话指的就是意识,不是你的意识或我的意识。
普:每当你假定意识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时,你就在假定一个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
阿:所有已知的是否都是意识的一部份?在这里,意识是当觉知来讲的。
普:克的观点和吠檀多哲学最大不同就在“意识”这两个字。吠檀多哲学认为意识是先于万物存在的能量。
阿:这不可思议的创造识能称为“柴坦亚”(chaitanya)。吠檀多哲学说这能量就是万物的根源。佛法却不这么说。佛陀对于宇宙的源头只字不提。原因是一谈论它就会落入空想,而空想和真实的修行无关,因此徒劳无益。
克:无明虽然没有开始,但是有办法可以结束它。不要探索无明是怎么生起的,而应该去弄清楚结束它的方法。
阿:现在立刻出现了一个问题。
克:很好,请你提出这个论点。
阿:佛法认为:“根本没有意识这个东西。无明没有开始,但是无明可以断除。不要探索无明是怎么开始的,因为空想只会浪费时间。然而无明又如何才能断除呢?无明就是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意识就是无明,这点我们必须好好讨论一下。
相信吠檀多哲学的人会告诉你,你所谓的“无明”其实就是宇宙识能的本质。它不断更新自己、不断创生,所有的成、住、坏、空都是它的展现。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接受佛法的观点,不可能立刻接受你所说的“无明没有开始,但是可以结束”。这两种观点是互相冲突的。
克:无明是没有开始的。这点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和意识领域里很清楚地看到。
普:如果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领域,那么它和拥有这无明记忆的脑细胞又有什么分别?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脑细胞以及它们的活动是可以测量的,而意识是无法测量的,因此这两者是不同的。
克: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脑细胞和它们的活动是可以测量的,而意识是无法测量的。
阿: 我可不可以建议一点?当我们通过最大号的望远镜来看宇宙时,我们看到的是这架机器允许我们看到的范围。如果再拿一个更大的机器,我们就有更广的视野。而意识却无法测量,因为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和它产生关联。因此我们不能说意识可测量或不可测量。它根本是无法讨论的。
克:没错。意识是无法测量的。普普刚才问的是:在意识之外还有没有和意识无关的境界存在?
普:在脑细胞里有没有一个无法分割、不可思议、无法利用的境界存在?
克:阿秋吉!你了解了吗?“不可思议境界”指的是全新的、不为人知的境界。
阿:我现在正要讨论这点。我刚才所说的意识是人类所有新旧记忆的源泉。脑细胞有能力立刻认出那些由种族记忆中产生的东西,那些存在过去已知的记忆领域中的东西。
普:几百万年以来所累积的已知事物。
阿:即使是最早期的人类记录,脑细胞都有能力记住。
克:等一等,请简化一点。我们起初讨论的是意识的范围,只要在意识范围内的都是已知事物。那么有没有存在于意识范围之外,也在脑细胞之外的未知领域?如果是在已知之外的领域,有没有办法辨认?如果是可以辨认的就一定是在已知领域之内。是不是只有当所有可以辨认的经验过程都停止,这个未知境界才会出现。普普的问题是:这个境界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如果是未知的,那么它在不在脑细胞之内?如果是在脑细胞之内的就是已知的,因为脑细胞不可能容纳任何新东西。脑细胞里的东西都是传统的、旧的东西。
我想再挖得深一点。在脑细胞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说有的。但是任何经验和思辨的过程都是在已知领域之内,而所有企图脱离已知的探索以及这类的脑细胞活动也都属于已知范围。
莫:你如何知道有一个未知领域?
克:你无法知道它。在那种境界里,我们的心是不辨真假的。所有已知的活动都停止了。
阿:那种境界和思辨及经验的过程有何不同?
普:两者的性质有何不同?
克:在那种状态里,所有的脑细胞和有机体仿佛都死去,然后就焕然一新完全不同了。
普: 让我用另一种不同的讲法。你说当时所有的思辨过程都停止了,但那仍是一种活着的状态,那么在那种状态下有没有存在感?
克:“存在”这两个字不太贴切。
阿:那种状态和深睡有什么两样?
克:你所谓的“深睡”是什么意思?
阿:在深睡中思辨和记录的活动也是停止的。
克:两种状态截然不同。
普:那么在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里,感官又处在什么状态呢?
克:感官暂停。
普:它们难道不运作了吗?
克:在那种状态,如果苍蝇飞到我的手上,我还是会抓一抓手,但这个动作却不影响那种状态。
莫:是不是还是知道自己在抓手?
克:当然。让我们慢慢讨论。任何已知的活动,包括意识范围内的经验、需求、渴望,甚至包括渴望解脱在内全都停止了,然后截然不同的境界才会出现。前者有动机,后者没有动机。通过动机是无法进入那种状态的。因为所有的动机都是已知的。因此我们能不能告诉自己:“探索宇宙的源头是徒劳无益的,我只知道如何断除无明。无明就是意识的一部分,无明就是想要获取更多经验的需求。”当这种需求停止了,是看清楚以后自然停止的,而不是通过动机、意志力和别人的指导而停止的,那么截然不同的境界才会出现。
莫:就算此刻你还是处于那种境界,你自己知道吗?
克:当然知道,我照样看得到你穿的衬衫,甚至能很清楚地看到它的颜色。五官还是照常运作,而认知的能力也相当正常。那种境界同时和这一切共存,并没有主客的对立。
莫:知识包不包括在内?
克:不包括。我必须很仔细地表达。我知道你们想要捕捉的是什么,我想使它尽量简化。
阿:即使这种解脱的本身也会阻碍我们捕捉到它,因为我们立刻就落入了主客的对立。
克:阿秋吉,你到底想捕捉什么?
阿: 我正在指出沟通所产生的困难。我认为那种境界是无法沟通的。我正试着去了解和我说话的这个人的心智状态,他是以什么作为根据来告诉我那个境界的?
克:那个根据就是:当所有的认知活动都停止了,所有从经验中得到的东西和动机全都断除时,这个人就从已知中解脱了。
莫:也就是没有认知的纯然觉性。
克:你所说的是另外一种状态。现在只是暂时脱离那种状态而已。
莫:你指的是暂时脱离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时间这个要素呢?难道另外还有一种时间存在吗?
克:让我们从头开始。脑子是在已知领域中活动的,也就是认知的活动。但是当你的脑子、你的心完全寂静时,你并不知道自己的心处在寂静中。如果你知道就不是真的寂静,因为那样就有一个观察者在那里对自己说“我知道”。我们所说的“寂静”是无法以分辨心来认识的,也超越已知经验范围之外。现在出现一个人,他企图通过语言来告诉你这不可思议的境界。当他一开口表达时,他就从寂静中出来了。那种寂静的境界其实一直在人们心中,然而只有那些彻底洞悉已知事物的人才有能力见到这种寂静。那种境界一直都在,从来没有离开过。处在那种境界的人仍然可以表达自己,但是却不离那种境界。
莫:你为什么要用“表达”这两个字?
克:本来就是在表达啊!
莫:是谁在表达?现在还是有一个人在对我说话啊!
克: 因为脑细胞已经有了语言知识,因此现在是脑细胞在表达一切。
莫:脑子有自己的观察者。
克:脑子本身就是观察者,也是操作者。
莫:那种境界和你现在的状态有何关系?
克:我先假设它们之间没有关系。事实是这样:脑细胞保住了那些已知的事物,当脑子完全寂静安宁下来时,就没有任何语言或妄念。那么这种脑子和不可思议的境界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莫:脑子和那种境界是通过什么力量衔接上的?你是如何办到这点的?
克:如果我说我不知道,你会做何答复?
莫:那么你不是天生带来的能力,就是别人赋予你的。
克:让我们再从头开始。这整个过程是意外或例外的吗?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就在此。如果这是个奇迹,那它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果它不是奇迹,不是从天而降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这种事只在这个人身上发生,而不在别人身上发生?
莫:我们能做什么?
克:我的回答是你什么都不能做—当然并不是“一事不做”的意思。
莫:这两种“不做”有何不同?
克:它们的不同在于:“一事不做”是虽然想达到那种境界,却不采取行动。“什么都不能做”则意味着只是如实观照每一个起心动念,而不空谈理论。
莫:你是说“什么都不能做,只是观照而已。”
克:如果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莫:这就把空想体悟落实下来变成了修行。
克:你必须非常非常安详地观照自己,无论行、住、坐、卧都是如此。这样你的感官就会变得很轻柔,日子过得就会很轻松。每分每秒都进入一个更深的境界。我有没有回答你们的问题?
普:你没有非常确切地回答我们。
克:让我们换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我们暂时称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为“无限的能量”,而一般人的能量却总是处在冲突和奋力中。当冲突完全没有了,处在那种无限能量里就可以随时更新自己。大部分人所知道的都是会消失的能量,而融入无限能量的情况却鲜有人知。
数千年的记录
普: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如何保住愤怒、恐惧或其他强烈的情绪,而不产生任何意念。我们能不能再深入一点来探讨?如果我们能达到上述情况,我们才能洗刷意识里的伤痛、恐惧、愤怒等等黑暗的东西。
克:把愤怒或其他情绪保住是什么意思?有可能吗?
普:有没有任何东西是没有名称的?
克:请继续。
弗:有没有一种恐惧是没有“恐惧”这个名称的?如果有的话,这种生命的能量又是什么性质?
阿:定名通常是为了能清晰思考。当我们在探索一种强烈的感觉或困扰时,我们总想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我们不想造成任何的自欺。因此名称既是我们的工具,又是困惑的原因。
克:名称就是事实吗?“门”这个字和真的门有何区分?“门”这个字显然不是真的门,因此名称不是事实。
苏:问题就在我们有没有办法指出真相。
克:我们将会慢慢地讨论。
拉:“恐惧”这个字眼不是真的恐惧,“门”这个字不是真的门,这两种东西好像不太一样。
克:真相能不能说明字眼?没有字眼,真相又存不存在?
苏:如果恐惧没有名称是一种什么感觉?
克:让我们慢慢讨论。字眼和真正的情绪、情感有何不同?
拉:字眼就是意念。
克:因此意念就透过字眼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如果没有字眼,意念能不能表达自己?当然,透过手势、眼神、点头等等姿态也能表达。但表达的程度就很有限了。如果你想表达一种非常复杂的理念,字眼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字眼到底不是真相。
阿:我们必须透过感官来接收讯息,当定名的活动一开始,觉知就停止了,接着一连串复杂的字眼就在我的脑子里出现。如果我把这些字眼去除,感觉还是存在的。
克:阿秋吉,你说的我不太能确定。普普吉问的是:能够保住感觉而不产生意念的心智具有那些特质?
拉:我们质疑的是这种心智能否存在。
克:没错。
普:意识里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在字眼之前产生的。
拉迪:原始的恐惧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能保住它而不产生意念吗?
普:我所说的不是如何保住恐惧,我是指其他的感觉,譬如温柔、欢乐。
克:你们能不能观察我这个形体,而不带有意念的活动?
普:可以。
克:你说可以,但是你现在已经在观察我的形体,表示你已经带有“形体”的念头了。
普:我们正在“观察”,我可没说是在观察你的形体。
克:好,那么你观察的是什么?
普:你知道,先生。你只要一说“我正在观察这个形体”,脑子里就一定会产生定名的活动。
克:就一定会有一个名称。
普:就一定会有定名的活动。
克:不一定。
普:请听我说,先生。当我说只有“观察”时,你的形体就成了我观察领域中的一部分。我是在观察,但是不只是观察你的形体而已。
克:我刚才是建议你把“克”这个字去掉,只是观察他的形体而已。当然你是在真的观察,但是你能不能只是观察他的形体而已?
普:好,我现在就在观察你的形体。
克:你想证明什么?
普:我想看看在观察之前有没有意念产生。
克:普普,简化一点!假设恐惧产生了,我想弄清楚是不是这个字眼制造了恐惧感。十年前我有过一次恐惧的经验,我的脑子就记录下了这种感觉及这个字眼。今天同样的情况再度重现,于是认知过程立刻透过这个字眼而产生。因此是这个字眼使我联想起过去的恐惧。字眼激发了感觉,固定了感觉。
拉:并且保存了感觉。
克:如果没有这个字眼,还会不会有恐惧的感觉?字眼就是认知的过程。弗莱兹!如果你现在正在害怕,你是如何知道自己正在害怕的?
弗:透过定名才知道的。
克:如何知道的?
弗:因为我以前害怕过,所以现在才能认出那种感觉是害怕。
克:如果你认出来的,它就是一种文字的过程而已。如果你认不出它来,那又是什么状况呢?
弗:那就不是恐惧,而只是身体的一种能量了。
克:不,先生,不要用“能量”这两个字,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另一个东西。假设没有认知,没有意念活动,恐惧还存在吗?
普:存在的是不安的感觉。
克:让我们掌握在“恐惧”这两个字来讨论。
普:恐惧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因此不好讨论。
克:当然,其中有很复杂的东西。
普:它是一种不得了的东西。
苏:在心理上,通常字眼还未出现,感觉就已经有了。
普:恐惧可以是非常深刻的东西。
苏:如果我们说字眼制造了恐惧感,似乎意味着恐惧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
克:我们的意思不是这个。我是说如果没有认知过程,恐惧又是什么?我不是说这种深刻的感觉不存在,我是说如果脑子没有记录的过程,也就是不储存记忆的话,那么所谓的恐惧又会是什么?
普:把“恐惧”这个字眼拿掉,看看剩下的是什么。换上其他任何形容词都会暗示“恐惧”这两个字。
克:我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的。你污辱我,我就立刻把这件事和这个字眼记录了下来。如果你污辱我,我什么也不记住,又会怎么样?
苏:这是完全不同的过程,不是我所能了解的。
克:其实是一回事。被人污辱的感觉也有恐惧。我们能不能不储存这种恐惧?下一次无论产生什么感觉,都不联想到过去?
拉迪:在恐惧的字眼出现以前,我们已经认出这种感觉了。
克:不,慢一点。我污辱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记住这件事,对不对?
拉迪:我一开始认出你的污辱,我就已经记住它了。于是就制造了一种业力。
克:那么就停止这种业力。我们能不能按兵不动?拉迪,让我们简化一点。假设你从小就受到各种伤害,脑子把这些经验全都记录下来。你直觉的反应就是不想再受到任何伤害,于是你就筑了一道墙,然后退缩在墙后。如果没有这道墙,你会知道自己受伤了吗?下一次当你受伤时,你能不能只是觉察而不加以记录?
弗:你所谓的“记录”是什么意思?
克:我们的脑子就是一架录音机,它永远都在录音——喜欢或不喜欢、欢乐和痛苦等等。它不停地录来录去。所以我才建议停止这种录音的活动。以前虽然有这种习惯,从现在起能不能不再录音?
弗:这意味着不立刻形成一种意象。
克:不,现在不要把意象扯进来,这会使事情更复杂。如果记录的活动不停止,我们的心、我们的脑子就永远不得解脱。
普:脑子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不可能不记录。重要的是当我们不动时,我们就脱离了记录的活动。
克:这就是我的意思。
苏:你们是不是在说两件事:一个是不动,另一个是彻底停止记录的活动。
克:发问之前请先弄清楚我的问题。
普:你说不记录,那是不是指脑细胞的活动完全停止了?
克: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停止记录,脑子就愈来愈机械化。
阿:我觉得你们把这个问题过度简化了。其实感官的作用和好恶一点关系都没有,反而恐惧是早就存在的。恐惧和感官是直接相连的。
克:只要脑子不停地记录,它就在知识中动来动去。我认清所有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四分五裂的,因此我问自己,这记录的活动能否停止?
嘉:脑子本身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克:我想能够。脑子能觉察自己的记录过程。
普:有一些恐惧可以靠觉察来解决。但是原始的恐惧已经深藏内心数千年之久,就很难对治了。
克: 我们的脑子数千年以来一直在记录恐惧,记录就变成它的功用,于是就愈来愈机械化。如果这种记录的活动不停止,脑子就只是一具机器,而人类也就永远无法解脱了。
帕尔: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脑子为什么要记录?
克:为了安全感,为了踏实感。记录活动能使脑子觉得安全。
普:但是透过记录的活动,脑子本身也在进化。
克:它是透过知识进化的,知识就是记录下来的东西。
普:有什么因素可以使它停止?
克:必须有新的挑战。也许有人会说:喂!人类透过知识进化了数千年,和老祖宗猿类已大不相同了。另一个人却说:喂!只要你仍停留在记录的活动中,你的生命就是四分五裂的,因为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因此你就永远会有痛苦和折磨。那么这数千年来的记录活动能不能停止?
普:如实地聆听和停止记录有没有关系?
克:有的。
普:如实地聆听就能停止脑子的记录活动。
克:完全正确。这就是我的论点。
弗: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有关脑子的记录事宜。重点是脑子本身无法停止自己的记录活动,那么要怎么办?
克:我们将会找出答案。首先我们应该听清楚这个问题。
苏:意识之中难道只有记录的活动吗?
克:当然。
苏:那么,那个能观察自己的记录活动的又是什么?
克:除了你问的这个之外,还有一种寂静的状态,那就是两个妄念之间的空档。
苏:两个妄念之间的空档,是不是也算一种记录的活动?
克:当然是的。
苏:“记录”这个字眼和寂静怎么可能相同?
克:凡是用意念诱发、透过意志力达到的寂静都是机械化的,因此和记录的机械活动相同。
苏:但是有时我们也能感受到非机械化的寂静。
克:非机械化的寂静不可能是短暂的。
拉吉:非机械化的寂静有可能来到吗?
克:这个我没兴趣讨论。我要说的是另一回事。意识的活动和局限全部属于过去的记录、经验、恐惧、欢乐等等。这种种活动如果不改变,我们就永远是四分五裂的。
拉吉:只有不执著于它,这些活动才可能停止。
克:不对,这些活动就是你,你和它并无分别。你就是这巨大的业力,这些传统中的偏见、共业以及所谓个人主张。如果这些不停止,人类就没有未来。如果有未来,充其量也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
普:因此心一动,无明就产生了。问题是意识的内容既然都是无明……
克:停止,等一下。
普:这是什么意思?
克:你的脑子能不能停止活动?还是,活动只是一个概念而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仔细地听着。是真的有活动,还是我们认为它是活动?如果活动不是概念,不是结论,那么脑子就能直接接触到这些活动。然后它就可以说:好!就让我看着它。因此你不必执著于停止这些活动,你只需要观察就好。你就是这巨大的业力,这句话是真的,还是一种概念?
拉吉:不是概念,是真的。
克:过去的活动能不能在当下这一刻停止,如果不能,痛苦就没有止境。像轮回或因果之类的解脱都无济于事。那么,这巨大的业力可以不透过控制而停止吗?
普:我们能观察得到吗?如果我们能观察到当下的感受,我们所观察的又是什么?
克:如果我骂你“傻子”,你就必须把这句话记住吗?
普:我无法回答你为什么必须要记住它。
克:不要记住它。
普: 这就要看我的眼睛和耳朵能不能不攀缘,不认同这个字眼了。如果我能静静地聆听,我就不会记住它。只剩下聆听,而没有记录的活动。
克:好,你看清了什么?
普:我发现如果我听自己说出来的话,这些话就会反弹回来,被我的脑子记录下来。如果我的眼睛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的耳朵只是静静地听着,那么所有的话就不会被记录下来。
克:因此你认为安静是最重要的条件,但大部分人都不安静。
普:可是我仍然无法回答你:为什么必须有记录的活动?
克:不,我说的是如果有人骂你傻子,你根本就不必记住它。
普:你的意思是,有的可以记住,有的根本不必记住。
克:不对,你其实永远都在记录。
普:只要我的感官攀缘于外境,就一定会有记录的活动。
克:“只要”这个字眼好像有“你现在不在记录”的意思。
普:我只是在解脱而已。
克:我只想知道这巨大的业力能不能停止。
普:任何一种解说或结论你都不接受,那么就只好想办法停止这业力了。
克:我问的是,要如何停止它?
普:现在我们就必须讨论脑细胞的记录活动了。
克:脑细胞发现业力能给它极大的安全感和保障,因此它才不断地记录,对不对?
普: 请听我说。其实业力只有一种活动,那就是透过从前的活动,接触到当下这一刻,然后延续下去。
克:过去的一切和当下这刻相遇,然后就修正自己,延续下去。脑子很清楚这是一条非常安全的沟槽。然而要如何才能使脑细胞清楚,这安全的业力其实最危险的活动?因此,为脑细胞说明它的危机就是当务之急。只要它一认清自己的危机,业力就会自动停止。你们能认清这个实质的危机吗?
普:你的脑细胞现在正在告诉你这个危机吗?
克:我的脑子只是利用这些话来告诉你们这个危机,它本身没有任何危机。它已透过观照而把一切都放下了。当你看到一条眼镜蛇时,你会立刻避开,因为你的脑子已受到数千年的局限,认为蛇就是危险的象征。你永远依照这个局限而做各种反应,立刻采取行动。其实质真正的危机不是蛇,而是你的想法。这种思想的业力一直延续了数千年,因为脑子在其中能得到安全感。一旦脑子清楚了自己的危机,就会立刻把这种业力放下。
拉吉:我不像你那么能感受业力的危险。
克:为什么,先生?
拉吉:因为我从未观察过业力的活动,因此认不出它的危险。
克:业力和你有分别吗?
拉吉:没有分别,先生。
克:你就是这业力,因此你观察的其实就是自己。
拉吉:没错,但是我观察自己的机会很少。
克:你能不能随时随刻觉察自己的业力活动?你也许会说:我有时候可以看到那悬崖。如果你指的是“悬崖”这个字,而不是真的悬崖,那么你就不可能看到真正的危机。“悬崖”这个字眼会不会制造恐惧感?
拉:不会。
克:不要立刻回答我,慢慢来。字眼不是真相,“恐惧”这个字眼不是那真实的感受?如果没有这个字眼,被称为“恐惧”的那个东西还存在吗?但是我们的脑子总是拒绝接受新东西,它会立刻说那种感受就是“恐惧”。为了使脑子能看到自己的业力,就必须在两个意念间留下空档,不去干预当时的感觉。字眼不是真相,你必须深入探索才可能产生空性。我不知道你们明白了没有?
普:我们能保住当时的感觉,比如仇恨、愤怒或恐惧,而不产生妄念吗?
克:当然有可能,试试看。
普: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呢?
克:不论什么原因,只要恐惧一生起就立刻保住它,而不产生任何念头的活动。
普:那又是什么情况呢?
克: 这样你就不会联想到过去的恐惧,而只是保住了那巨大的能量。如果巨大的能量被保住而没有任何念头的活动,爆发性的突破就会产生。然后你的生命就彻底转化了。
如果觉得《心智 意识 脑细胞(上)》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