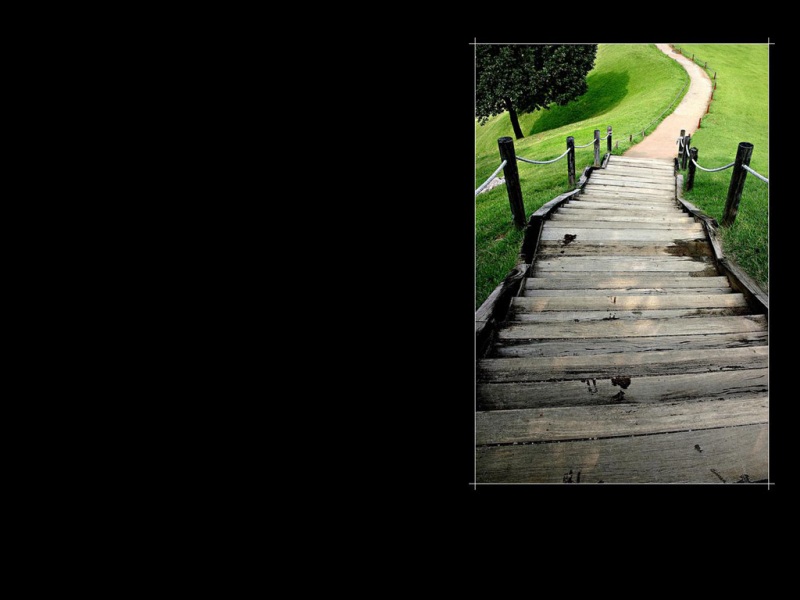署名及版权声明
1936年的某一天,上海马思南路(今思南路)梅兰芳公馆里,有过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主人是梅兰芳,主客是刘宝全,作陪的有梅的秘书许姬传和梅的两个学生。
当代青年怕是很少有人知道刘宝全了。他是上世纪上半叶全国知名的京韵大鼓的大名家,享誉40年的曲艺界艺术前辈,人称“鼓王”。1936年梅兰芳是42岁,而刘宝全已经67岁,他们的关系,用刘的话说:“您(指梅)生下地办满月酒那天,我就到李铁拐斜街(梅家)老宅里走堂会,光阴似箭,一晃四十多年啦。”梅答说:“……您是看到我长大的,真是好几辈子的交情了。”梅比刘小25岁,当然是后辈,但这时他在京剧界已是如日中天的首席大家、戏曲界领军人物。一个鼓界大王,一个伶界大王,一次称得上空前绝后的艺术对话,我想称之为中国演艺史上的一次双峰聚会,应是没有疑问的。
这次聚会的谈话过程由许姬传等记录整理,用梅的名义写成题为《鼓王刘宝全的艺术创造》的两万余字的长文。我不知道何时何处首发,但收入1962年出版的《梅兰芳文集》中,问世至今也有50年。我也不知有过多少有关此文的评介,我觉得现在还是值得再次向读者推荐,因为这实在是一篇有光彩也有思想的艺术大散文。
梅兰芳前一天向许姬传等说:“明天请刘老吃饭,有几个意思,一则叙旧,二来要他谈谈京韵大鼓的源流,三是要请教他保护嗓子的窍门。”梅的目标很明确,也很专业,实际上也可以说这一次谈话是梅兰芳在促进和帮助刘宝全总结他一生的艺术经验。
在这次交谈后,梅兰芳还和其他熟悉刘派鼓书艺术的人“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归纳为六点,写在本文的最后。六点的小题是,(一)艺术生活化;(二)吸收姊妹艺术丰富创造;(三)鼓套变化运腕灵活(鼓套大致是指击鼓的程式套路);(四)开门见山,余音袅袅(指书词结构的谨严);(五)创作改编的得失(讲刘所有书目在文学上的得失);(六)声乐创造的卓越成就。在距今半个多世纪之前,像这样的人物所做这样的艺术总结,我不知道在曲艺史上还有没有别的例证,我是没有见过。无论如何,这是今天的戏曲曲艺从业者所应该习读的大文。
由于这是梅兰芳发起的会谈,也由于刘宝全在少年时曾演过京剧,这篇文章中时时闪烁着的京剧与大鼓两种艺术交互作用的亮点,成为贯串全文的一根彩线。刘宝全说,他在北京有点名儿,曾应邀到谭鑫培家中为他“聚精会神地唱了两段,谭老板听完了,把我叫到他身旁,拍拍我的肩膀说:‘唱得不错,好好儿干,有饭。’”又说,他在北京的住处附近“都是梨园行名角,像谭家、‘老乡亲’(孙菊仙)、龚云甫、宝忠的父亲杨小朵……我一边和他们往来,一边抓功夫听戏,琢磨他们唱念做派的韵味神气”。
在具体演唱艺术上,刘对京剧的腔调、念白如何运用到大鼓里作了介绍。他说:“大鼓书一向在《马鞍山》里使用二黄腔,《南阳关》里唱一段西皮调……至于大鼓里夹‘上口’的念法,以前是没有的,因为我学过京戏,所以加进去了。”梅兰芳为他补充说,“大鼓里没有‘嘎调’之说,可是您唱《大西厢》,‘崔莺莺’三个字就等于嘎调。”这是指唱。而在做工方面,刘宝全更明确地说:“当然要从戏里去找门道。把许多好角的身段神气记在心里,择了用,原封不动搬过来是不成的。”总之,“刘先生常说,他的表演得力于京剧者十之三四。但从表面来看,一招一式,究竟是模仿哪一个名演员,并不能立刻指出,他吸取过来后,已经变成自己的东西了。”
梅兰芳从两方面看问题。他“了解到刘先生京韵大鼓艺术表演体系的形成,得力于吸收京剧的表演艺术,而我们京剧界受到刘先生鼓艺的影响,也有不少生动的例子”,“前辈中有谭鑫培、孙菊仙、龚云甫、杨小楼、王瑶卿先生等,都是爱听刘宝全的大鼓书,并且吸收了他的东西,丰富了本身的艺术”,“据我知道言菊朋、马连良先生都曾下功夫揣摩刘先生的唱腔、用气、运嗓的方法而得到收获。”
不仅演员的演唱,就是乐队伴奏上同样需要彼此学习。梅兰芳说他的琴师徐兰沅、王少卿“都非常喜爱刘宝全先生的大鼓书……并且吸收大鼓的声腔和三弦四胡的伴奏技巧运用到京剧里”。
梅兰芳于此说了一段极重要的话:“也有人认为刘宝全的大鼓虽好,但究竟是一种说唱艺术,掺到京剧里未免贻笑大方。我不同意这种狭隘的门户之见,京剧一向是吸收各种曲调来丰富创造的,那么大鼓书何以不能采用呢?这要看运用得当与否,才能判断成败。”梅兰芳这段话虽是因刘宝全而发,实际上是他一项重要的演剧思想,也是中国戏曲曲艺的基本经验。
刘宝全的艺术借鉴,并不止于京剧,曾为他伴奏三弦的白凤岩就说过,刘的《大西厢》中“二八的俏佳人懒梳妆”等唱腔中就采用了梆子的腔调,但融化得好,听的人不容易觉察出来。梅兰芳也介绍说刘“还通晓其它曲艺,……我们要求他唱一段梅花大鼓、快书或者时调小曲,他也欣然歌唱”。既然通晓,自然就可能融汇贯通,适当吸收。
而梅兰芳,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更明确说过,他从小就爱看戏,“所以我常常把多看戏的好处介绍给青年演员,希望他们什么行当的戏都看,什么剧种的戏都看……做一个演员,就是要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避免别人的缺点,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演技。”这不仅是梅兰芳的演剧思想,其他许多京剧大家都是热衷于艺术上的广泛交流。这番话使我想起盖叫天就是个苏州评弹迷,周信芳不仅迷评弹,自己还演过话剧,程砚秋更是有计划地多次调查和观摩多种地方戏。
这篇大文章内容丰富,还涉及大鼓和京剧的演唱技巧和艺术方法问题,如何保护嗓子问题,以及与知识分子的合作问题(对许姬传说“干咱们这一行,离不开你们文墨人”)等等,至今犹可回味。
这次双峰聚会离现在七十多年了,缅怀当时情状,一个全国性戏曲剧种的青年艺术家,一个地方曲种的老年艺术家,相对而坐,你问我答,我说你笑,娓娓而谈,真诚畅快。到了吃饭时,晚辈梅兰芳给前辈夹了一块四喜肉到他的碟内,“刘先生把这块肉夹起来还敬我说:‘我一向不吃肥肉,如果一定要我吃下去,回头诸位听《刺汤勤》就是四喜肉味儿了。’”由此又说了些保养嗓子的习惯,“肥肉虽能养人,但是生痰助火……烟酒辛辣,我是一概不动的。”
一个儒雅求教,一个老成倾谈,从家常故旧谈到剧种交流,从技巧细节谈到艺术哲理,整个过程充溢着亲切、真挚和学术探讨的气氛,到现在想象起来,还是令人神往。
我们当前浮躁的演艺圈,能不能从这样的双峰聚会中取得一些感悟呢?(来源:文汇报-02-26第八版,作者:刘厚生)
前面提到《鼓王刘宝全的艺术创造》一文,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刘宝全先生晚年有一次到上海(一九三六),在“大中华”演唱(大中华饭店在西藏路,楼下有一个专门演唱曲艺的场子),我去听他的《长坂坡》,演毕,到后台向他道乏,并约他第二天到我家里吃饭。我还约了许姬传和我的两个学生作陪,就对他们说:“明天请刘老吃饭,有几个意思,一则叙旧,二来要他谈谈京韵大鼓的源流,三是要请教他保护嗓子的窍门,你们帮我把他的话记下来。”
那天上午,刘先生带着儿子到了马思南路我家的客厅里,我扶他坐在沙发上,恰好对着壁上挂的我祖父巧玲先生写的一副隶书对联:“知我便当良友待,斯人况以善书名”。他仔细端详了对上的句子,笑着对我说;“您北京住过的几处宅子我都到过,您生下地办满月酒那天,我就到李铁拐斜街老宅里走堂会,光阴似箭,一晃四十多年啦。”我说:“当年我的祖母和姑母常对我谈起这件事,您是看着我长大的,真是好几辈子的交情了。”这时,我搀他到隔壁饭厅里吃饭。我们一边吃菜一边谈。
我说:“我们这一界都爱听您的大鼓书,每逢家里有人过生日或者办喜事,总得请您辛苦一趟。我记得早年听别人唱的大鼓,字音带保定、合间的口音,所以称为“怯大鼓”,打您起才变了,讲究字音,怯味儿十去八九,‘怯大鼓’变为‘京韵大鼓’,是您的功劳。”刘先生谦虚地说:“谈不上什么功劳,就是给我们这一行把马路放宽点,走道方便些。”
我接着说:“以前大鼓书的唱法是平铺直叙,起伏不大的,翻高唱也是打您行起来的,比如《长坂坡》上场七言八句里:‘……灯照黄沙天地暗,那尘迷星斗鬼哭声……’。这里‘鬼哭声’翻高唱,就把战场上阴风惨惨,鬼哭神嚎的味儿唱出来啦。请您谈谈‘怯大鼓’是打哪儿来的?您是怎么琢磨着改成现在的味儿的?”
刘先生说:“‘怯大鼓’是从直隶河间府行出来的,起初是乡村里种庄稼歇息的时候,老老少少聚在一起,象秧歌那样随口唱着玩,渐渐受人欢迎,就有人到城里去作场。早年最出名的是胡十,他的嗓子又高又亮,外号‘一条线’。他先在直隶一带卖唱,以后到天津,就更红起来。”
刘先生接着谈他幼年学艺的情况。他说:“我原籍是直隶深州,生在北京,九岁时就在天津学大鼓,因为我的父亲也是唱‘怯大鼓’的,我一边学大鼓,还爱拨弄三弦,我那时的身量还没有三弦高,定调门,转弦轴时,还要人帮忙。以后,我又改行学京戏,在天津科班里坐科,第一次到上海演唱,在台上出了点错,我非常懊恼,回到天津就拜一条线胡十做师父,胡十善唱文段子,他把玩艺儿都教给我,发音用气得他的传授最多。还有两位老先生,霍明亮武段子唱得好,宋五的《马鞍山》是一绝,我都跟他们学过。”
按 白凤岩先生说,刘先生所说台上出错的情况是这样的:刘先生与师兄在上海合演《空城计》,师兄扮司马懿,刘先生扮诸葛孔明,当孔明在城楼上唱完“闲无事在敌楼亮一亮琴音”。下面弹琴一笑后应接“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刘先生忘了这句,净等司马懿接唱:“有本督在马上观动静,……”而司马懿却等他唱这下旬,彼此愣了一会,台下就有笑声。到后台,刘先生埋怨他师兄,师兄说:“你缺了一条腿,我怎么接呀!”刘先生当时感到十分惭愧,就向他师兄道歉。以后改回来仍唱大鼓成了名。
白先生又说,胡十善唱抒情段子如《大西厢》、《蓝桥会》、《王二姐思夫》……,霍明亮擅长《战长沙》、《单刀会》……战争故事,宋五除了《马鞍山》外,《截江夺斗》、《火烧博望坡》也是拿手。这三位前辈的玩艺儿,有极好的,也有一般的,可以说是金沙杂陈。刘先生披沙拣金地吸取了他们的菁华,发展创造而自成一派,直到今无还是京韵大鼓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
刘先生继续述说受京剧界老艺人的指点和影响。他说:“我在天津一带唱大鼓渐渐有点名儿,就到北京卖艺。谭老板(鑫培)的大儿子常听我的大鼓,有一天到 后台来邀我到他家唱给他的老爷子听。那天我聚精会神地唱了两段,谭老板听完了,把我叫到他身旁,拍拍我的肩膀说:‘唱的不错,好好儿干,有饭。’我请他指 点,他说:‘你是唱书,不是说书,还有口音带点怯,北京的有些座儿恐怕听不惯,作艺的讲究随乡入乡,你是聪明人,自己回去琢磨吧!’”
刘先生谈到这里,神情激动地说:“‘一字为师’,谭老板这两句话,比金子还值钱。我以后就照他的话来改,我把怯味儿改成京音,唱腔也和弹三弦的反复推敲, 让它细致大方,并且琢磨着连唱带说的气口,耍着板唱,这样,脸上的神气和身段也不同了,至于翻高唱,我是试着步儿来的,先偶尔用一两句高音,台下座儿很欢 迎,以后就练高音,但是用三弦吊嗓,出音不够高亮,我有时兼用胡琴吊嗓。那时,我住在北京石头胡同天和玉客店,前后几条街住的都是梨园行名角,象谭家、 ‘老乡亲’(孙菊仙)、龚云甫、宝忠的父亲杨小朵……我们都是朋友,我一边和他们往来,一边抓工夫听戏,琢磨他们唱、念、做派的韵味神气,我用胡琴吊嗓, 大半唱《回龙阁》里薛平贵唱的‘长安城内把兵点……’或者《打金枝》里,唐王唱的‘景阳钟三响把王催’一段,有时还试着吊《四郎探母》‘叫小番’的‘嘎 调’。”
我打断了他的话头说:“京戏里的‘嘎调’是另一工劲,我陪谭老板(鑫培)唱过几次《四郎探母》,‘叫小番’的‘番’字,他使假嗓,炸音、微微带点沙音, ‘扭回头来叫小番’这一句完全用丹田气直喷出来,‘扭回头来’下面不加‘空匡’换气的锣鼓,叫人听了真解气,并且和杨四郎拿到令箭,急于回营探母的戏情抱 得很紧。‘嘎调’的音必须准确,如果够不到工尺,音就‘黄’了,所以要用假嗓,使丹田气,懂得这个窍门,可以百发百中。大鼓里没有‘嘎调’之说,可是您唱 《大西厢》,‘崔莺莺’三个字就等于嘎调,但大鼓是不能完全照京戏的嘎调唱的,您是从本嗓转到‘立音’,好听极了。咱们内行所说的‘音堂相聚’,就是真假 音接榫的地方听不出痕迹来,没有真工夫是唱不上去的,您不但上去了,而且唱得那么悠扬宛转,真是不容易,有人说您的嗓子是‘云遮月’,可以比得上谭老板, 这句话一点也不算过分。我从幼年到现在,足足听了您三十多年,您在我家里走过多少次堂会,是来的客人都爱听您的大鼓,这位点一段,那位烦一段,您一天唱过 大小六段,您的嗓子总是那么圆润清亮、韵昧酵厚。您是怎么保养得那么好?请说一说。”
按 白凤岩先生认为刘先生的《大西厢》“二八的俏佳人懒梳妆”以及“崔莺莺”的唱腔,采用了梆子的腔调,但融化的好,听的人不容易觉察出来。
刘先生说:“有句老话‘干一行,怨一行’,我却不然,我是真爱大鼓,每一段里的每一个字,一个腔、一个音,我都细细琢磨过,张嘴大小和每个音应该从哪儿发 出来,怎么使劲,都有准谱,这是巧劲,翻高唱可别使浊劲,要让人听了好象不费劲,才算玩艺儿。梅老板您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嗓子经久耐用,宽亮好听。我 们靠嗓子吃饭的人,最忌使浊劲,不但听了笨,没味儿,而且还毁嗓子,有些人忽然嗓子哑了,就是没有找到用嗓子的门道,几十年来,我的嗓子只是比较上有点出 入,可是没有哑到一字不出,我说的使巧劲,有个重要的关子,就是要会用气,第一要练丹田气,至于提气,换气,偷气……种种门道,都要下功夫自己揣摩。懂得 养气的道理,才有长劲,唱个五六段是不会露馅儿的。”我接着说:“您说的对,有句老话:‘内练一口气’。我觉得嗓子好比喇叭、唢呐上的‘哨儿’,要用气吹 才能响的,象我们唱旦角这一行的,往往中年塌中,嗓子倒了,那并不是嗓子坏啦,其实是气力不足,催不动嗓子,所以高音就没有了,老辈常说蹓湾儿、吊嗓都是 为了‘长气’,这和您的说法是一样的。”
刘先生很高兴地双手合拢来一拍说:“对啦,唱戏、说书全靠精,气.神,讲究稳、准、狠,必须要‘开窍’,就怎么来都合适,窍门是要下苦工琢磨才能打开的, ‘天上掉下馅儿饼来’的事情是没有的。开了窍,还得练,不能缺工。我每逢上台的日子,早晨一定把当天所唱的段子,在弦子上过一道,一则溜噪,二来温习词 儿,几十年来从没有间断过。至于保养嗓子的办法,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不过是饮食寒暖,格外小心而已。”
这时,端上一碗四喜肉来,我举箸夹了一块布到他的碟内,刘先生把这块肉夹起来还敬我说:“我一向不吃肥肉,如果一定要我吃下去,回头诸位到大中华听《刺汤 勤》就是四喜肉味儿了。”他接着说:“干我们这一行,和唱戏还不同,《二进宫》是唱工戏,可是三人轮流着唱,《玉堂春》虽然一人唱到底,也穿插着王金龙的 唱、白,和布政,按察二司的问话,并且每一句慢板,原板里都有过门隔开,可以休息,而大鼓书的座儿是专为听唱而来的,身段表情只能作为陪衬,讲究一口气要 唱几十句,嗓子有一点不合适就顶不下来。所以最怕嗓子起痰、咳嗽,吃东西就不能不特别小心,肥肉虽能养人,但是生痰助火,我的保养嗓子的办法,只是吃得清 淡些,上台前不要过饱,晚场唱完后,才踏踏实实地吃一顿,烟酒辛辣我是一概不动的。”
我听了他的话,不觉悚然有悟,在旧社会里,有一种风气,剧团从北京到外码头旅行演出,主要演员须要拜客,当地的头面人物就设宴款待,这种应酬一直延续到演 出后,如果请而不到,得罪了“大亨”、“闻人”,就会引起麻烦,我往往在出台前赶一两处饭局,虽然不敢多吃,但饮食方面却不能象刘先生那样一丝不苟地保护 嗓子。
饭后,我们回到客厅里坐,我倒了一杯新沏的北京香片茶,递给刘先生说:“您今天讲了许多经验之谈,我们增长了不少学问,您饮饮场,歇会儿再给我们开讲。” 他笑着对我说:“您享这么大的名,还是那么谦虚,真是了不起。说到学问,我的书本工夫有限,全靠朋友帮忙,我的座儿里,藏龙卧虎,真有高人,我常常请教他 们,我现在讲一段故事给您听。”
刘先生喝了一口酽茶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认得一位做蒙古买卖的李三爷,他爱听大鼓,自己能唱,有时高了兴,在饭馆里唱一段,嘴里讲究极啦。我每次登 台,他总在台下听,他手里托着水烟袋,闭目凝神,好象睡着了一样,听到得意的地方,微微点头,唱得不惬意时,就摇摇头,这就等于叫倒好。我在台上做活时, 十分注意他的神气,唱完了就亲自到他家里去请教,他一点也不客气,哪句唱得好,哪个腔使得不合适,哪个字太浊,哪个字太怯,都告诉我,我记在心里,照他的 话来改,受到益处可不少呀。”
我说:“象李三爷肯说,您肯听,彼此都够交情。我刚出台时候,也是遇见几个热心朋友,我每天唱完戏,他们就到我家里,象师父教训徒弟那样,‘择毛’、‘挑 刺’,哪点儿神气不对,哪个身段别扭,哪个字音倒了,哪句词句欠通……,这位讲完,那位接着说,我都记下了。还有人看了戏写信来,也是尽挑眼,我记得初演 《汾河湾》,接到一封信,有五张信纸,大意是青衣虽然要稳,但也不能太板,柳迎春更要会做戏,当年时小福演《汾河湾》的柳迎春,就从水袖里伸出手来做戏, 称为“露手青衣”,他还接着剧情,出了许多主意,我再演时,有些地方就照他的意思做,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不断来信,就交上了朋友。”
刘先生说:“李三爷的脾气,也是挺古怪的,必须再三追问,他才肯说,座中有他瞧着不顺眼的人,他象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的。”他沉吟了一下,接着感慨地 说:“李三爷的年纪比我大,早已下世去了,现在年轻人里有些爱听大鼓的,也用心往里钻,我的词儿都记熟啦,有时改几句词儿,或者换一个腔,他们都听得出 来,象陈十二爷(彦衡)的儿子富年,就能操起鼓板唱一段,给您拉二胡的王少卿会弹三弦,杨宝忠拉四胡,他们仨人凑在一起还真象那么回事。”
……
讲好每一个故事
如果觉得《【曲海】梅兰芳对谈刘宝全:民国演艺史上的一次双峰会》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