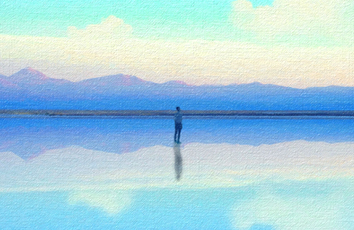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通讯员 马正心
西北偏北,是目前定居在杭州的诗人和作家张海龙的生身之地,也是他的长成所在,更是他的流离之所。
而男人带刀,可能是生存法则,也可能是故作强硬,更可能是刀锋行走。你知道的,每个带刀的男人都有故事,全与爱恨情仇有关,那是武侠小说里的人物设定。而在现实当中,刀需要藏锋不露,甚至需要心中有刀而手中无刀,因为一分锋利就是一生锋利,勇猛精进,是年轻时的张海龙对自己以及文字的要求。
十年前张海龙的那本随笔集《西北偏北男人带刀》又再版了,拉拉杂杂地讲了许多凌厉往事。而今,这位西北偏北男人人在江南。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至中年,我从兰州一路奔走,随波逐流来到杭州。”
当然,这一次巨大迁徙,也让张海龙有了重新审视自己的所来路径的理由。
以下,我们就来听听“西北偏北”男人张海龙自己讲述的人生故事——
张海龙在自己的“诗外空间”工作室。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有一根脐带与母体相连,呱呱坠地其实就是剪断脐带迎风成长,从此独自去面对所有的未知以及可能。事实上,无论我们走出多远,都有一根隐形的精神脐带始终牵系着从前,牵系着亲人和故乡,牵系着哭泣与欢喜,牵系着离别与欢聚。
西北偏北,是我的生身之地,也是我的长成所在,更是我的流离之所。而男人带刀,可能是生存法则,也可能是故作强硬,更可能是刀锋行走。你知道的,每个带刀的男人都有故事,全与爱恨情仇有关,那是武侠小说里的人物设定。而在现实当中,刀需要藏锋不露,甚至需要心中有刀而手中无刀,因为一分锋利就是一分凶险。
英国小说家毛姆在《刀锋》开头有此引言:“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他的意思是,人的肉身是难以逾越刀锋的,但凭借精神的强大或可突破。毛姆写完这书不久,他最爱的人就与世长辞。是的,在这苍茫的人世间,我们始终不能理解和接受的,就是无所不在的“痛失我爱”。刀锋,隐喻的是众生皆要面对的无常之苦。悲欣交集,才是智者终能领悟的终极命运。
从前的书里,我记下了太多与命运有关的“短制”,都是些小故事,看着却惊心动魄。我刻意地保持冷静,想用零度写作的方式勾勒出那些“生存之地”。再版的书里,我补充了一些新的故事,命名为“众生”,又加入了“诗篇”以及“诗人”两个单元,是想以此为凡庸的人间笔记作出一份“总结陈辞”——
仅仅一堆故事是不够的,那不过是穹顶之下的众多事故而已,我们必须看见命运。
诗篇,才是救赎之道。正如“万物都有破绽,是为了让光涌入”。
诗人,替我们活着,也替我们死去,更替我们去说出真相。
如今时常呆的地方,是良渚文化村。
2
接下来,我想说的就是来时路,那是一根无尽的精神脐带。
年岁渐长,生活过很多地方,我开始形成一卷根深蒂固的“私家地理”。言下之意,就是你生活过的地方会对你影响深远,你的气质会不由自主地向其靠拢。换句话说,你在哪条街上长大,你就在哪条街上成人。你在哪个故乡出生,你就被哪个故乡捆绑。你别无选择,你也无处可逃。
拿我自己作例子: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五人,前面四个都出生在海拔2780米的青海格尔木。在这块非同寻常的高地上,格尔木是句蒙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境内有大大小小几十条河流。格尔木是座荒凉得可以足不出户的城,却是这世上辖区面积最辽阔的城。它由柴达木盆地和唐古拉山乡两块互不相连、中间相隔400多公里的辖区组成,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英国,一个福建,两个宁夏。
这是座兵城,也是座汽车城,更是一座游牧之城。无数的淘金客、冒险王以及体制的流民不断涌入又不断流出,上帝的沙盘上一直行走着这些自不量力的挑战者。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生如草芥来去自便,不用过于计较得失成败,也无须太多蝇营狗苟。在寥廓的戈壁上,在无边的大城里,在钴蓝的天空下,在消融的雪线边,人只会放下妄念与虚狂,懂得自己的渺小和谦卑。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家一路迁徒,沿着河流走向,重返祖籍甘肃。1973年,我出生在兰州市西固区河口南。我们家来自“河流密集的地方”,顺流而下,照样还是与河流紧邻。黄河一脉泥流浊浪,自星宿海而来,穿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在此与洮河、湟水、庄浪河、咸水河四水交汇,逶迤而下,向东疾行。山逼河来,河劈山去,直接切割出一线纵贯四十多公里的兰州谷地。
的确如此,河流与天命都是一样的川流不息。被河流裹挟,就是被海洋召唤,我们这家人如同大水漫漶,不定期地溢出原有的河道,涌向这个国家被冲积出来的“泥浆文明”。我哥像块礁石被永久地湮没在兰州河谷,我大姐去向福建厦门,我三姐落定山东龙口,我二姐和我扎根在浙江杭州。回望来时路,溯流再向上,真是件让人惊奇的事。我们家所有的流动轨迹,都如同河流从高原顺势而下,分流南北,借着自然蛮力,从此再不回头。
夏日,我首次入藏,火车进去汽车回来,返程时途经格尔木,那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曾经生活过的城池,那自然也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城前,茫茫八百里荒漠戈壁早让人眼酸心荒。格尔木硕大、空荡、通透、寂静,没来由地令人怅惘以及苦楚。在城里吃饭、撒尿、兜圈、拍照、抽烟,隐隐然却有种到了自家地界般的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参加青藏汽车团,在这里修建青藏公路,也在这里娶妻生子。几十年过去,青藏铁路修进西藏,却功能性地黯淡了格尔木。回兰州面见老爸,和他说起格尔木见闻感受,听他散淡忆及当年青海往事。种种生活图景,故事旁逸斜出,诸多细节难辩,难以勾划全貌。如同大河裹挟泥沙滚滚而下,谁还能想见源头的清澈与细弱?
年初,老爸突然重病不起,哥哥将他送入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我和姐姐们分别从三地飞回兰州,从机场拉着箱子直奔那座就在黄河之畔的医院。我们在病房里没日没夜守护了整整一周,终于还是没把昏睡中的老爸唤醒。自始至终,老爸都沉默得如同身边那条河流,我们竟没有机会和他说一句话。
逝者如斯,或许,他就这样回到了河流的源头,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而我们远行的这些儿女,竟然不能更完整清晰地描摹他的一生。
我们走得太远,再也难寻源头,是为最大的悲伤。
3
人至中年,我从兰州一路奔走,随波逐流来到杭州。
刚到杭州买楼,或是宿命所致,被开发商的广告一下迷乱了心神:“双水岸,纯生活。”话说是那小区被两条河流相拥,一曰西塘河,一曰潘塘港河,正是想象中的江南生活。没怎么犹豫,我就下了单,看着眼前挖出的大坑遥想未来的诗意栖居。
一直等到住进去,才发现“双水岸”果然不假——小区两侧真的各有一条逼仄小河,其中一条横在我楼下,蛙鸣鱼跃,波澜不惊。“纯生活”当然也是真的——因为这是个郊区孤盘,周围任何配套设施都没有,最近的超市也在四公里之外,学校以及幼儿园都还只是画饼,真的只能过最纯粹的生活。当时心中暗叹,江南确是人文功底了得,硬是凭修辞把一处荒园说成天堂。
江南风水虽好,只是藻饰过多,地名颇多甜腻,让我这个北人好比公牛闯进瓷器店,多有尴尬之处。你说,我每天上班的地方叫什么名字不好,偏偏叫个什么胭脂巷!哇呀呀呀,我这个体重两百斤的虬髯大汉出没于此成何体统,平白减弱了我天纵的不羁豪情。好在,住地始终有河流相伴,也大体符合我的命运走向。水流所向,从来随遇而安,且行且看吧。我名字中有个“海”字,万水归一,莫非就是要我带着所有河流一路奔波到大海?
再之后,我在杭州换房而居,又搬至京杭大运河边的丽水路上。窗前日日而过的,是大运河上满载泥沙与货柜的大船。经常在夜间,大运河上十几艘乃至更多货船头尾相接成长龙,船上有人鸣笛喊话穿梭前行。让人梦里依稀感觉身处客地他乡,仿佛落地玻璃窗的客厅就是夜航船头,有种停不下脚步一直向前川流不息的惶恐。
搬到大运河边不久,我又被河流裹挟而去。看到台湾人唐立淇的星座书上说,我要居住在一堆奇形怪状的建筑物旁边,生活仍要变动。咄,刚刚迁入运河边新居,怎么可能我再与搞怪建筑为邻,这星座书不是乱讲话么?再说了,我住的地方旁边岂能无河?怪屋又关我何事?正不解间,答案突至:我接到任务要去上海世博会中国民企馆工作一年。到了上海,直接住进浦西世博园边上耀江花园十七层高楼,向前百米之外就是浪奔浪流的黄浦江。这无可辩驳的事实以及无可避让的命运,让我对星座学顶礼膜拜,简直就是大神显身一般不可思议。
在上海工作那一年,世博园外还有一处办公场所,位置正设在西藏南路上的“丽园”。我一看这两个字就笑歪了嘴——这“丽园”真是和“胭脂巷”有的一拼!中间加个“春”字,我就是《鹿鼎记》里的混世顽童韦小宝,笑嘻嘻赖兮兮出没于红粉世俗之中。生活从此充满俗世欲望,每天花样纷繁同时也漏洞百出,你只有足够强大才能抵挡堕落与诱惑。这其实也正与河流相近,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大河,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携带能力”才能冲积出平原,并且最终归入大海。
你瞧,我随波逐流,混浊生动,是为传奇和尘世而生。这是我的私家地理,也是我七印封存的命运之书。人人生而有命,每个人的故事一出生就已经写好。说到底,有些事早就安排好了。你不用算命,命早就在算你。
青年张海龙。
4
西北偏北,乃是一种伟大的庇护。需要逆流而上,去触摸和拜谢一座城市。
这些文章,最早是给报纸写的一个专栏,那个专栏名叫“西北偏北”。文章里写的这些西北旧事,大多与一座叫兰州的城市有关。我在这座城市里出生、长大,然后离开、回望。我在这座城市里体味了太多的东西,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全在其中。一座城市,也像一个人一样,自有它的筋骨和血肉,也自有它的温度与冲动。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脱离开一个具体的地点去生活。我想写出这座城市里那些日常生活的传奇,它们的材料,来自于我的生活经验、道听途说、文本阅读以及虚构想象。
甚至,我在全世界的很多城市里都发现了兰州的蛛丝蚂迹——雅典的神性、曼彻斯特的宿醉、伦敦的自恋、爱丁堡的狂想、伊斯坦布尔的分裂、巴黎的文艺、威尼斯的迷失、杜布罗夫尼克的创伤、日内瓦的寂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粗暴、纽约的躁动、香港庙街的杂糅、杭州的享乐、广州的无序、北京的自大、重庆的江湖、乌鲁木齐的混血……是的,我在哪里都能发现那座城市的某个侧面,它灵魂附体几乎无处不在。
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后来有了专栏名叫“万物生长”。我想,我的笔下,也的确是写到了万物生长,我们可以在静夜时分,听到那些草木生长拔节的声音,听到那些花大朵大朵扑噜噜开放时的声音。那些故事里的主人公,和我一样游移不定,都呈现出一种卑微的生存状态。我们不露痕迹地活着,与万物一起生长,也与万物一样枯荣。《杭州日报》的编辑莫小米老师说,我的文章一看便是陇海线以北的,自有一种地气与血性存在,与江南的精致柔弱全然不同。这一点,我相信并且深以为荣。我捉笔如挥刀,那些黑压压的文字从来血脉贲张,仿若一群揭竿而起云集响应的义军。
我的绝大多数精神滋养都来自西北这座城市,它粗陋简单,却又真实动人,绝无一言难尽,只有一饮而尽。那是一座“匪气十足”的城市,它的特点是“怎么都行怎么痛快怎么来”,所以凡事都不能按常理去解释。我的很多文字都在寻找一个命中注定的主人公,就像叶舟那句诗里写的:午夜入城的羊群/迎着刀子/走向肉铺。那些羊群,几乎就是命定般的西北化身,是整个西北的一个隐喻。很多人,很多事,在西北偏北之地,都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就是如此这般,就是顺其自然,就是干一票大的再说,就是那么一个看得清清楚楚却无法说得明明白白的结果。
这样一种背景下去生活,似乎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何谓悲剧。在西北,你会很容易感觉到那种沉重苍凉的东西,与南方的轻飘浮华完全不同。就像穿过兰州的那条姓黄的河流,万物被它裹挟而下,可能半途蒸发,可能中道断流,可能奔流到海,也可能沉积成大地的一部分。河流下山,就必须不断向前,哪怕泛滥改道也在所不惜。
没有一条河流不是曲折前行的,它必须绕过各种障碍,才能一点点壮大自己。
没有人的生活不是跌跌绊绊的。我们必须不停地告别,才能真正地长大成人。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生命就是一条奔跑的河。改道,就是去顺应自然的法则。
从山上到山下,从旷野到城市,从这儿到那儿,从此岸到彼岸,从大陆到大海,从一种风景到另一种风景,从我到你——这是一个奔跑和抵达的往复过程。生命如同河流,停滞就是终点。不是变,就是死。
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大象无形,似动为动,最好的生命状态是不疾而速,这又是河水流逝带给我们的另种启示。
是故,王阳明才会说:“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人生苦短,必须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最精准处,从心髓入微处用力,才会终有所成。
十年之功,可以面壁亦可以磨剑,可以洗心更可以革面。更好的选择,是可以结缘和发愿,是把这册文字在于我最看重的城市出版,而且竟是以“活字”的系列与名义。
再次向所有朋友致意,正是你们的烛照,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西北偏北男人带刀,将成为我们共同的标签。
如果觉得《夜读|西北偏北诗人自述:带刀的男人 都有爱恨情仇》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