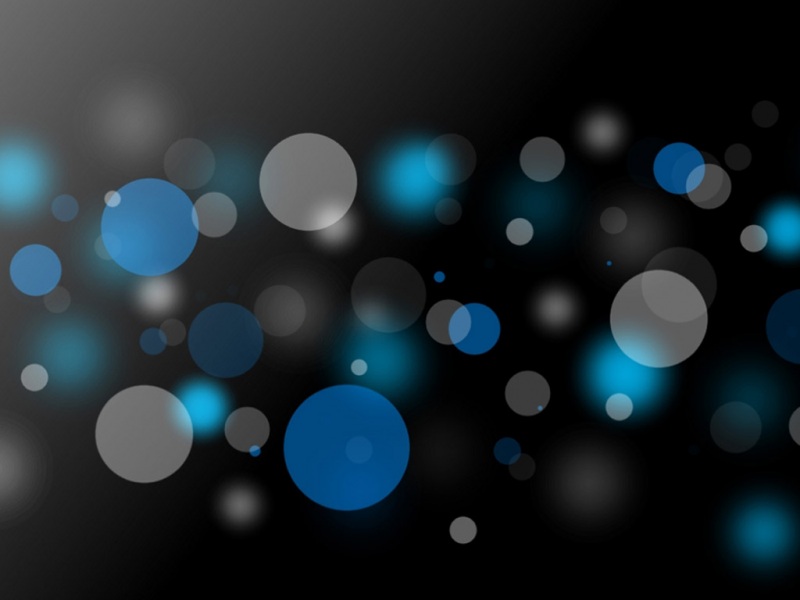异域源头活水来
———域外诗选序
文/北塔
一、域外和域外诗概念辨析
“域外”这个概念的含义有泛义和狭义两种。这取决于人们对“域”这个字的理解和界定。“域”的本义是“地域” “区域”,可以泛指任何一个空间范围,如 “城市”“陆地”“海洋”甚至“天空”。覃子豪在题为《域外》的诗中说:
域外的风景展示于
城市之外、陆地之外、海洋之外、
虹之外、云之外、青空之外
只要在某个区域之外,都是“域外”。
国家也可以被理解为“区域”。特定意义的“域外”指的是“国外”,即“国境线之外”,也可称做“外国”或“异国”。
因此,“域外诗”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外国诗”。如施蛰存选译的《域外诗抄》就是他翻译的英、美、古希腊、波兰、西班牙、法、比利时、丹麦等八个国家的诗作合集。此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10月推出(印制质量较差,多年后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善本)。稍早,198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规模不小的“域外诗丛”。到1991年,出版了多种,都是外国诗歌的汉语译本,影响颇大,本人就买了其中几种。或许由于急忙推出,有点慌不择译,有些诗的译文不忍卒读。
本书中“域外”指的就是“国外”。因此,本书中没有一首诗、一篇文章是关于港澳台的。
我们之所以不用“异域”这个概念,是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里,这个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异国,即外国;二是泛指华夏王土以外的所有番邦,包括周边的异族政权。而不同的异族政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华夏朝廷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情况,有时是在行政上直接归属于华夏朝廷,有时是完全独立于华夏朝廷,有时是貌合神离(名义上归顺了,实际上自成一体,哪怕进贡也是为了得到多倍的赏赐)。笔者以为,只要外藩没有真正纳入中原行政体系,完全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比如像越南、朝鲜、日本等历史上所谓的附庸国 (或称 “附属国”),都可以称作“域外”
以上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谈域外诗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还可以从创作者经历的角度谈域外诗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作者在任何地方(包括本国)所写的外国题材的诗歌,这些题材可以来自直接经验也可以来自间接经验——比如道听或阅读;即,只要题材是外国的,都可以算作域外诗。狭义指的是作者必须有外国游历的直接经验,对笔下所处理的事物,必须眼观其形,耳听其音,身临其境,不管体悟是深还是浅,他所表达的必须是现场的体悟。比如,魏源一生创作了近900首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西洋名物的,如 “夷船”“夷技”“洋琴”等,居然有近90首是关于大英帝国的鸦片的。因为他是林则徐禁烟运动的得力干将,所以颇为了解鸦片,也多谈鸦片及其危害。但是,魏源的足迹最远只到过澳门和香港。所以,我不同意有些学者把魏源的这些所谓外国物体的诗归入“域外诗”。假如这些也算域外诗,那么现在中国满大街都是洋货,写这些洋货的作品就都是域外诗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还有一个例子是明末清初尤侗的 《外国竹枝词》。尤侗(16—1704年)是苏州府人,算是我的同乡先贤,才学了得,曾被顺治皇帝誉为 “真才子”,被康熙皇帝誉为“老名士”。有不少人说,他的《外国竹枝词》是中国诗人最早创作的外国题材竹枝词专集,所涉及的国家还颇多,主要有今日本、印度、索马里、孟加拉国、埃及、西班牙、阿富汗、肯尼亚、土耳其、沙特、伊朗等;但由于他老人家从未曾出国,其写作的资源全部都是文献资料(怪不得他那么早就可以涉笔那么多国家);所以也不符合本书对域外诗的定义。
总之,域外诗指的是中国诗人根据自己在国外的亲身见闻所写的关于国外题材的诗。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脚踏出国门(不包括在国内写外国事物),第二个必备条件是所写必须是外国题材(外国元素越明显越合格,如果没有外国元素则基本不合格),黄遵宪所谓 “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如果要放宽一点的话,还可指寓居国外的中文诗人所写的关于他所处国家和中国之外的题材的诗。因为我们认为,界定诗歌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国籍,不如说是语言,更不如说是文化、思维和观念。域外诗可以有而且我们鼓励要有中国的文化、思维和观念的元素,但不应该以中国元素为主,而应以外国元素为主。中外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互补,也可以冲突。冲突可能更有认识价值和美学张力。
二、中国域外诗写作的第三次高潮正在到来
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对外交往都在加强。中国人包括中国诗人出国的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密。
当前中国诗人当然没有被掳到域外的,也没有为了建立军功而投笔从戎到边疆去行军甚或打仗的,也极少外交官等食禄者一边出去公干一边写诗。那么当代中国诗人有哪些出国途径呢?
(1)官方派遣出访。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部以及各地作协等文化机构时不时派遣或大或小的代表团出访。这类出访的特点是层次比较高,人员比较少,考察的国家和地方也比较少。官方派遣出访的代表团中不乏诗人。他们都写下了域外诗,但总体数量不多,质量也不太令人满意。这可能是因为体制内的大部分诗人本来就有内在的束缚,再加上参加的都是官方的活动,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比较繁杂,导致诗人们在异域环境中从言行到思维都相对谨小慎微,缩手缩脚,缺乏诗歌创作所需要的那种意兴湍飞、灵光亢奋的氛围。当然,这只是就域外诗写作的条件而言,与此类代表团出访的主旨并无大碍,对出访的成功也没有影响,因为出访的目的是交流,而不是创作,域外诗只是出访的副产品,甚至可以说是诗人夹带回来的一点“私货”。
(2)1980年代初,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后,出国留学的人数井喷式增长,有的毕业后选择定居甚至入籍在外国。留学生中不乏诗歌爱好者,有的后来成为相当成熟的诗人。留学生诗人群体庞大,素养较高,他们写了非常多的域外诗。
(3)中国的对外贸易极为繁荣,每天有大量商务人士出境,去参加展览或谈判或看货,其中有些是诗商,他们在商业活动之余,会在域外读书写诗。本书中的梅尔和倮倮就是这样的代表。
(4)这些年很多诗人(包括集子里的所有诗人)都有出国旅游的机会和经验,这种旅游跟家里人甚至陌生人同行,那种场合的主观诗意取决于个人,几乎没有相互激发的可能;因此,在那种情况下写作诗歌的动力不够,域外诗的创作数量也不多。本书中的陈波来曾经当过国际导游,旅游对他来说也是商务。他在辛苦万分的工作行旅之余,还坚持写诗,难能可贵。本书中的赵剑华和王桂林等都有亲属在国外,从而有过探亲游的经历,也都有诗为证。我本人曾经带着家人专程从缅甸去柬埔寨的吴哥窟,写下一大组,也是可观的收获。
(5)还有一种更稀少的但不能忽略的,是在极特殊时代语境下由于极特殊原因,某些诗人或完全迫于压力或半自我流亡到域外,并且比较长时期地甚至可能大半生都会在外漂泊,时不时为了生计而变换住地;哪怕长期定居在某地,在精神上也可能有流浪感。他们写有大量域外诗,而且质量都相当高,成为古今中外异常发达的“流亡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6)随着文化学术交流渠道的多样化,中外诗人之间交往的许多民间窗口被打开。这种民间模式可以分为个人和群体两种。有些中国诗人直接被外国同行所关注并受到邀请,他们遂以个人身份出访,或参会,或进修,或演讲,或攻读学位。
这类出访诗人名额极其受限,每次每场一般只有一到两个,也形不成内在的激励创作激情的氛围,他们的域外诗写作也比较有限。中国诗人参加由民间团体组织的对外诗歌文化交流活动是诗歌专业的活动,而且由专业机构举办;参加者一般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的行为,但这类机构和组织都是民间的,而非官方的。比如,世界诗人大会是非政府组织,几乎每年都在某个国家或地区举办年会。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是其衍生机构,中国代表团都由办事处组织。
大致在之前,中国诗歌的对外交往以官方系统为主,之后则以民间为主。现在我们就以世界诗人大会及其中国办事处所做的为例,说说民间的优势。第一,民间的参与人数比较多。官方的每个代表团只有两、三位或至多三、五位诗人,民间的则可以有十多位甚至几十位。第二,民间的访问目的地比较多,官方的现在一般一次只有一个国家,民间的可以一次就有三、五个。第三,民间的较少拘束,出访氛围更加轻松、更有诗意。第四,民间的相互关系比较随意,可以互相肯定,也可以相互批评。这样有利于作品的大量产生,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自从本人首度组织并率领中国诗歌代表团访问匈牙利并参加世界诗人大会以来,尤其是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成立以来,我们已经组织过十几次外访,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10余年来,我们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已经组织三百多人次的中国诗人前往欧洲、亚洲、美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各类诗歌活动,而且不局限于世界诗人大会年会,还参加过不同国家的国际诗会,出访了许多国家,举办了许多场双边诗歌交流会,起到了非常好的交流效果。同样重要的是,团员们在出访过程中,不仅与外国同行相互学习,而且相互之间切磋、激励、鼓励。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写了诗篇,少则数十篇,多则数百篇。其中不乏金玉锦绣,甚至已经成为各自的代表作。我们需要甄选、集中推出。比如,我们在去考察了秘鲁的自然与文化双料世界遗产马丘比丘之后,所写的同题诗。有的在国内多家专业诗刊发表,有的还获得了比较重要的诗歌奖项。我们的十几个新老团友这么些年来所积累的作品,每个人都够出单本诗集。将来我们将以丛书的形式推出这些诗集。其他人的如果出成多人合集,也有好几本。这是仅仅就我们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所参与组织的成果而言。如果加上外面其他人的域外诗写作,总量是非常可观的。虽然现在来说,比晚清域外诗可能还差一截;但是,晚清一共有71年,而当代中国,如果从准备开放国门的1976年算起,到现在,才44年。如果从实质性开放的1981年开始算起,那么才39年。我们还有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多年时间进行积累。而且,诗歌外交转而以民间模式为主之后,无论是参与的诗人还是域外诗创作的数量,都在加倍增长。
我相信,最终当代中国的域外诗写作成就将比肩甚至有可能超过晚清。理由如下:
(1)当代出国诗人、出访国家、域外诗(行数,而非不具备可比性的首数)三个数量指标都正在或者即将超过晚清。晚清出外最多的诗人足迹抵达不过十余国,而当代有些诗人(比如我本人)已经涉足几十国。
(2)就诗歌的情感基调而言,更是如此。如果说东汉蔡文姬那时的域外诗的基本情调是悲怆,盛唐域外诗的基调是悲壮,晚清的是悲喜交加,那么,当前的基调是不悲不喜。中国传统的诗歌(包括晚清的域外诗)往往有抒情中心主义倾向,而现代诗突破了这种模式,变为以感想为主。所谓感想,是带着感情去思想,感情还在,甚至可以依然浓烈,但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在字里行间所表达的主导性主观因素是思想。“悲喜交加”还是感情主导或者说被感情主导,“不悲不喜”则超越了感情的主控,变成以思想控驭感情。
(3)就诗歌中的思想而言。盛唐域外诗以气势取胜,其中的思想比较单薄。晚清域外诗中有了一些观念,但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正统观念和华夷有别观念的严重影响,许多诗人要么崇洋媚外,要么对外界的新鲜事物左看不惯、右看不顺。他们中有个别人开始接触并拥抱自由平等的西方现代观念,但很难把这种平等意识用到中外交流中去,即很能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很能让两种文化展开平等的对话。而当代诗人做到了,我们能平视外国诗歌,深入而从容地与外国诗人进行对话。最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经常出国的诗人已经抛弃了崇洋媚外或贬抑夷狄的陈腐观念,而是不卑不亢地与外国同行进行平等对话,从而能从容地与外国同行商讨各类诗学内部话题。我们更能借鉴他们的思维方式,化用他们的思想成果。一次,当代域外诗所表现的思想更丰富、更深刻、更多元。
(4)就诗学而言,在鸦片战争十多年后,即1850年代,西方即开始现代主义诗学探索和实验。尽管在1880年代或迟至1890年代,黄遵宪等人已经长期在欧洲,而且担任参赞那样的高级外交官,但他们毕竟是在官场,而非文化界,所以对于文化先锋是隔膜、疏理的。因此,他们与西方当时先进的诗歌潮流是脱离的,并没有建立什么有效联系,并没有形成互动,并没有推动中国诗歌的现代化。黄遵宪等晚清诗人的诗学观念号称革命,但其实还在旧诗的观念范畴里打转,只是堆砌、玩弄一些新名词,涉猎一些新现象,或者加入点口语化的表达法,并没有实质性的诗学现代化主张和举措。当代中国诗人已经基本上与世界上的任何诗歌潮流同步,他们广泛地与外国同行交流,谦虚而比较充分地了解同行的所思所想以及所拿手的诗歌技艺。
三、当代中国域外诗之理论探讨
3.1 本土之解域化:域外诗与域内诗之别及其诗学意义
3.1.1 题材之别
域外诗写作首先意味着题材的扩展。无论是从整个域外诗写作史还是个人域外诗写作的角度而言均是如此。随着整个人类相互交通的开拓,我们所能抵达的地方越来越多,比如南美洲,晚清的人们是很难去的,现在虽然也不容易,但我们去了,收到了很好的访问效果。诗人骆英以登山的方式旅行,攀登了世界五大洲和南北极的最高峰,他的这些域外体验是极其罕见、无法复制的;而且他每次都写下了数量可观、质量可赞的诗作最后汇集出版,即《7+2登山日记》;这可以说是域外诗写作中的一部珍稀诗集。
异域题材的涌现是催化剂,或者说是诗歌创作的催情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创作的灵感源泉的活水,浇灌并养育我们的诗花,进而结出好诗的累累硕果。正如倮倮所自承的:“我向来也奇怪,为什么一出门就有诗,且天生异质,而呆在家里鲜少有诗从心里蹦出来,可能正是陌生和偶然激发了诗的灵感。”每趟域外诗旅都会让不会写诗者也会吟,让平素少产的诗人短时间爆发,成为丰产者。
3.1.2 境界之别
空间范围扩大必然带来境界的宽广化和高远化,导致或加速洲际意识、世界意识、宇宙意识和人类意识的产生。年青人凭借想像可能也会产生这些意识,但因为没有切身体验,往往显得空泛;卧游者、地图旅行者凭借知识的移植可能也会产生这些意识,但也因为没有脚踏实地而显得空洞;真正的域外诗写作者是在亲身游历了半个乃至大半个地球之后才产生这些意识,所以他们的这些意识是坚实的充实的实打实的。比如伊甸常住在江南一个并不算大的城市里,在游历了澳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之后,在走了欧洲多国之后,他在挪威的“松恩峡湾”写下极为豪放的诗行:
幸福和苦难,这一对命运的翅膀
扇过松恩峡湾,扇过大海和陆地
扇过欧洲和亚洲
也扇过你和我的头顶……
再如,阿诺阿布则平常偏居西南一隅,在他游历了美洲、亚洲多国之后,他在瑞典参观了斯特林堡故居之后,也以浪漫主义的笔法,以跟斯特林堡对话的口吻,对整个世界和人类揶揄道:
先生,我只得实话告诉你
欧洲跟上个世纪没两样
白天表现主义说了算
夜里是现实主义的天堂
人们和你恋爱的时候一样残忍
世界比你在世的日子更加荒唐
3.1.3 情感之别
优秀的域外诗,绝不仅仅满足于像游记一样去描摹事物或叙述事件,而是借域外题材以进行强烈的抒情、寄托自己的心思。晚清域外诗作者有数十位,为何黄遵宪一家独大?一言以蔽之,写心也。同光体诗派领袖陈三立盛赞 《人境庐诗草》,曰:“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此之谓天下健者。”“心”灵之赤诚,感情之充沛,是黄遵宪的域外诗最吸引读者的优势,也是梁任公散文巨大魅力之所在(怪不得梁也高度肯定黄)。域外诗的抒情性由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所奠定,也是历代域外诗所禀赋的,当代域外诗也依然珍视这一点。
就抒情气质而言,域外诗类似于唐诗,其主要场域是广阔的天地、壮丽的山川、奇特的景观,其事件是抒情主体在户外活动,其主题往往是人对时空的大跨度的感受。
域内诗则类似于宋诗,其主要场域是逼仄的官场、校园、家庭甚或书房,其事件是抒情主人公在人际中交往,其主题是对日常生活的敏感和把握。
目前中国诗歌写作的场域特征是宋诗的而不是唐诗的,有对生活细节、微妙情感的捕捉、刻画,有细微的甚至尖锐的感受,总体格局是期期艾艾,无病呻吟,受一点苦皮伤,就要死要活。没有让心灵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充分打开,与大事件的关联似乎是密切的,但由于心灵的自我桎梏,缺乏对大事件的穿越时空的拷问能力,只是把自我的日常情绪补缀在大事件上。
目前中国诗歌写作的场域特征是宋诗的而不是唐诗的,有对生活细节、微妙情感的捕捉、刻画,有细微的甚至尖锐的感受,总体格局是期期艾艾,无病呻吟,受一点苦皮伤,就要死要活。没有让心灵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充分打开,与大事件的关联似乎是密切的,但由于心灵的自我桎梏,缺乏对大事件的穿越时空的拷问能力,只是把自我的日常情绪补缀在大事件上。
黄遵宪之所以能成为“天下健者”,即成就他的情感的健朗特色,跟他丰盛的域外经验密不可分;正如盛唐气象端赖于开放的国家胸怀所吸纳的大开大阂的巨量“胡风”;当代域外诗写作应该也要有这样的气度和功用。
3.1.4 思想之别
当一种固定区域内的文明经历发育、成熟、烂熟之后,就会萎谢、没落,仅靠自身的力量,几乎没有自我反转、鼎革、升华的可能,尤其是受累于机制化的文明,其所在的区域将成为思想甚至思想者的监狱。这个时候必须有域外的力量加入,才能使固化的文明突破和新生。这域外的力量便是解放者,矫正和解救本土文明。域外文明作为他者是诗歌主体进行自我反思的场合、契机和资源,从而对板结的本土文明包括诗歌模式有可能进行解域化努力并产生积极效果。
因此,我们在域外总能够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思想,因为新思想往往来自异域的环境、异样的情境、异常的情景,新思想是思维的放假放出来的,是一桩惊喜的思维的外遇,甚至是一次意外的脑部孕育。
比如,我在罗马尼亚就有两度新思想的意外获得。一次是在布加勒斯特,我在参观齐奥塞斯库生前所建筑的号称欧洲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宫殿之后,突然得了飞蚊症。飞蚊是光明中的或者说是人类在对光明的追求中的一个黑点乃至污点。跟许多具有卡力斯马性格的所谓领袖一样,齐奥塞斯库生前也以光明的化身自居,他一直用彩虹般的伟大理想吸引乃至哄骗人民,直到人民最终发现他是一只飞蚊。我突然顿悟,写下我的域外诗代表作之一 《飞蚊症与齐奥塞斯库》。诗云:“甚至当我闭上眼/我也能看见它/像彩虹拉的一粒屎。”另一次是在比斯特里察,我在考察完一座教堂建筑之后,它已经不再是宗教场所而是文化场所。我觉得这座建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象征,似乎还有信仰,但信仰已经失落,已经被文化化,或者被文化所取代。没有信仰的文化只是知识意义上的,可以谋生;但很难让我们的心灵安顿其中。比如,诗歌这一文化形式,往往被作为一种准信仰,假如没有真信仰意识灌注其中,那么文本就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文字空间,正如没有宗教内涵的教堂只是一座信仰的空壳。文化是不可能真正取代宗教的,只能导致宗教的削弱、淡化乃至式微。这些思想,是我在域内不可能得到的。
在异乡,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念故乡,所谓思乡,一开始只是情感上的需要和关联,而思念总是甜蜜中参杂着苦涩甚至痛苦。久而久之,可能是痛定思痛,由情感转化或升华为思考,由对故乡的情感依赖,转为对故乡概念的彻底领悟。故乡概念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家乡,二是原乡。前者是我们曾经出生或生长的某个现实地域,它是物质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物质意义涉及地理、食物、动物、植物和气候等。文化意义包括语言、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原乡寄托的是我们的信仰、灵魂和终极关怀。也就是说,家乡是物质与精神双重的概念,而原乡是纯精神的概念;是众人的家乡或者说是众多家乡的公母。家乡是过去的,趋向于把我们往回拉;原乡是未来的,能够给我们提供前行的动力,让我们背负着思乡的重担而依然前行。中秋节,我是在德国慕尼黑过的。后来我写了一首关于月亮的诗。这是异乡的月亮,也是故乡的月亮。后者我用李白的月亮来指代,因此而赋予这个形象以故乡概念的所有含义。李白是中国的,而在外国,中国便是我的故乡。李白是文化的,所以李白的月亮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中国的象征。李白一生向往高高在上作为天国象征的月亮,因此,他是把月亮作为原乡来崇拜的。请看我的《慕尼黑玛丽安广场上空的中秋月》一诗中的一段:
我也会加紧脚步
从异乡到异乡
而那孤悬在天空中的
总是李白的月亮
当我们对故乡概念有了彻悟之后,我们思乡的时候就会多一份淡定与轻松。正如陈波来《在勒克瑙吃嚼烟》一诗中所展现的异乡客的形象:“而异乡客游走于街市与巷陌的步履,至今轻快、从容、甚而恰似那年的优雅。”
3.2 他者之自我化:域外诗与域内诗之同关乎诗歌的本质和诗人的个性
3.2.1 异域可以是反照自我身份意识的境遇
域外诗终究是诗,诗者,心声也,所以表情达意也。异域作为他者,给我们提供异乎寻常的题材、境界、情感和思想,最终都要通过主体的容器进行筛选、浸泡、过滤与化合———可总称为“心灵化”,都是为自我的完成服务的。因此,域外诗与域内诗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域外是他人的酒杯或杯酒,诗人喝酒,无论是洋酒还是土酒,都是为了浇灭自家心中的的不平或块垒。在陌生的异域,表面上我们走的是别人的路,看的是别人的风景,听的是别人的故事;但诗人的主体性是很强大的,他们从未曾迷失自我,而且还把别人的事物拉到自己的轨道上来。赵剑华《邦咯岛听道模吹巴乌》诗云:
真好,望着别人的星空,说自己的故事
在陌生的港湾,我们做了自己的海盗
我们始终是一只眼睛看着外界,另一只眼睛注视着自己的内心,充满反省意识。而这内心也没有因为外界事物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依然是善恶并存,天使与魔鬼时和时斗。于是,倮倮在韩国观览壁画时居然发出的是极为私我的感慨:
“尽管我知道我的心里也住着魔鬼
它们整天厮杀/天使暂时占据上风”(《下午游梨园洞壁画村》
自我的处境、命运以及在任何处境下的反应、任何命运下的招架,才是诗人关注的焦点。这种自我身份意识贯穿着诗人的任何一次游历,几乎贯穿着他的一生。伊甸的思想受到卡夫卡以来欧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极大影响,有着相当彻底的对自我命运的不确定感和无助感,有时他像卡夫卡一样拷问自己、审判自己,到了啮心的程度,因为他跟卡夫卡一样,敏感地认识到:在高度严密的现代社会制度之网中,我们的自我是不断退却、不断丧失的。《在卡夫卡墓前》,他以感同身受的口吻,与卡夫卡展开超越时空但真切到有点残忍的对话:
卡夫卡,你也在审判我吗?
我虫子一样怯懦,木偶一样顺从
冰块般僵硬和冷漠
我在不断地变形
我像风一样
失去了自己的形状和色彩
3.2.2 异域可以是返照国家身份意识的镜像
诗人一般都具有激烈的家国情怀,他的自我身份意识往往关联着国家身份意识。我们在国外遇到很多事情,不管是那个国家所独有的,还是本身就是国际性的,时常会联想到中国的某段历史或某个历史事件,从而发出对祖国命运的哀叹或担忧或期望,感慨万千。我写的大型组诗 《苦路———致耶稣》在开头直接把自我放置在那些参与审判耶稣或看客的位置上,从而把自我的个体人性和人类的普遍人性结合起来进行拷问和反思。我始终认为,“我”不仅是暴政或庸俗的受害者或牺牲品,“我”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或积极或消极地可能会成为“恶”的某种同谋或帮凶。后来,伊甸《在耶路撒冷》一诗中出于对现实的关怀,谴责道:
在耶稣被审判的地方
你发现那些审判者
正混在游客中嬉皮笑脸
他在写作同题组诗时,把“我”从同谋者或帮凶的队伍里抽离出来,成为一个旁观者,或对“恶”的潜在的历史审判者。我以为是降低了自我反省的程度。在那组诗的最后,我把反思的对象从个体自我置换为国家自我,在把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的比较中,力图回答为何我们甘当看客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没有爱憎分明的态度,喜欢在善与恶之间和稀泥。
当然,我们作为爱国知识分子,在很多时候对祖国的情感是单纯的爱恋和念想:
我不停地进酒,我怕停下
会忍不住流泪,感到更加孤独
会忍不住改变行程
马上回到祖国,回到杏花村去
———王桂林:《慕尼黑将进酒》
而作为诗人,我们更多怀恋的可能与其说是祖国的现实,还不如说是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将进酒”“杏花村”和“长安”都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指征。
3.2.3 域外诗的修辞策略让服于已经奠定的风格
本书作者基本上都是中年诗学的实践者,都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包括修辞策略。
我们都有着相对完备且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无论到哪儿,看到什么,我们都有话要说。修辞立其诚,我们只是用诗歌的修辞诚实地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钱锺书对黄遵宪的域外诗的评价可能有点过于苛刻,“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但我们念念在兹,引以为戒,力图在自己的域外诗中不仅有新事物,还有新理致,即对事物的新颖而深刻的理解。无论是懂外语的还是不懂的,我们都没有简单地抄写外文单词或懒惰地罗列事物名词,而是试图写出我们对事物的深刻感受,或者事物印刻在我们心上的影像。
域外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的另一个场域,我们用现代主义的诗学观念和技巧去处理这一不断丰富不断变化的现实。或者说,那是一块新的磨刀石,能够磨砺我们的诗艺,让笔锋更加锋利,但没有必要更换刀笔本身。
在域外诗写作中,在文本呈现的话语中,每个人几乎都保持着自己依然固定的风格,比如伊甸的稳健、倮倮的尖锐、桂林的密致、阿布的野性、梅尔的内倾、刘剑的外放等。本书的诗作修辞程度普遍比较高,但没有达到繁杂晦涩。意象丰富多样,但并不过于繁密。这些特征,无论是作为共性还是个性,都体现在每个人的域外诗文本中,没有因为是域外题材而出现走样。假如一个诗人非得要将就题材而改变自己的风格,我认为那是不成熟的表现。当然,小改不仅合法,而且应该。
北塔,现居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曾受邀赴美国、荷兰、蒙古等20余国参加各类文学、学术活动,曾率中国诗歌代表团前往墨西哥、匈牙利、以色列等10余国访问交流并参加诗会。
目前,已出版诗集《滚石有苔——石头诗选》《巨蟒紧抱街衢——北京诗选》,学术专著《照亮自身的深渊——北塔诗学文选》和译著《八堂课》等各类著译约30种,有作品曾被译成英文、德文、蒙古文等10余种外文。
如果觉得《行吟诗刊丨北塔:异域源头活水来》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