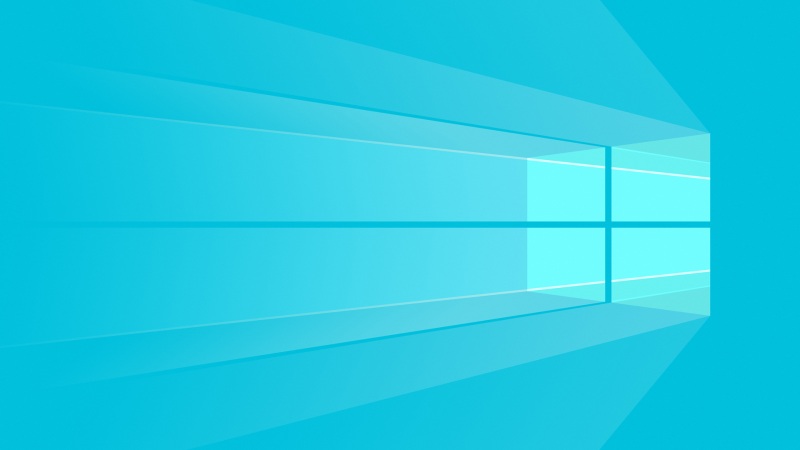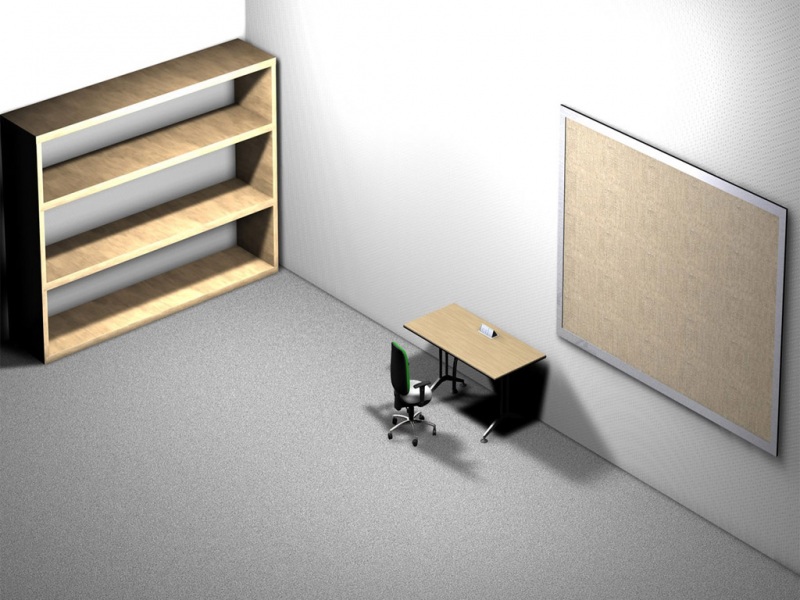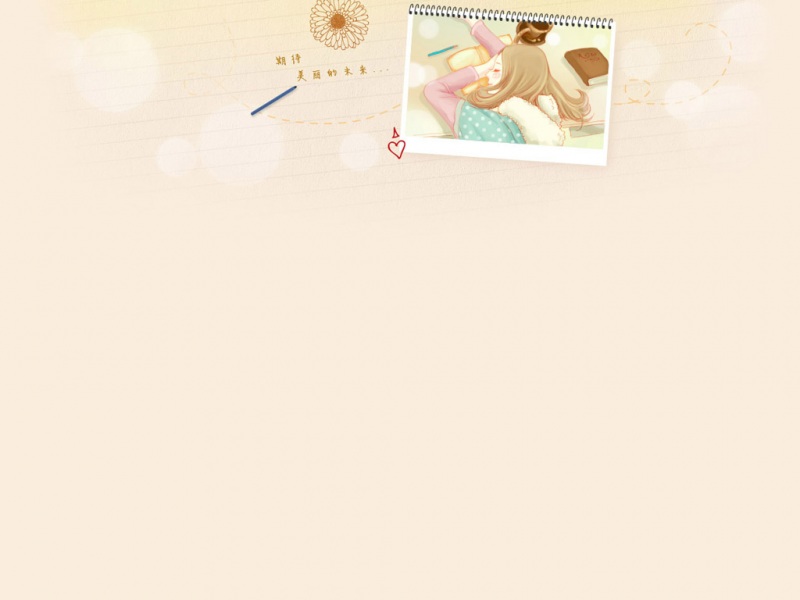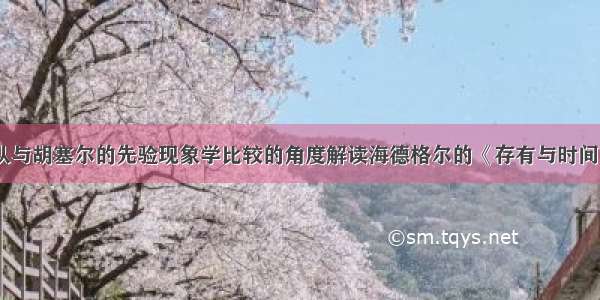
张庆熊:从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比较的角度解读海德格尔的《存有与时间》
核心提示:海德格尔的《存有与时间》是对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继承和批判。《存在与时间》中虽然出现了很多新的哲学词汇,但熟悉胡塞尔的学者会发现它们在胡塞尔那里有相对应的用语,如:“此在”(Dasein)与“先验自我”(transzendentale
Ego),“此在的结构”与“意向性的结构”,“我操劳”(sorg...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存有与时间》(Sein und Zeit)是献给胡塞尔的。[1]这不仅出于对胡塞尔的尊敬和友谊,更重要的是在提请人们注意他们间思想上的一种特殊关联。我读《存有与时间》的时候感到这本书的思路既来自胡塞尔又针对胡塞尔,它是对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继承和批判。《存在与时间》中虽然出现了很多新的哲学词汇,但熟悉胡塞尔的人会发现它们在胡塞尔那里都有相对应的词汇,如:“此在”(Dasein)与“先验自我”(transzendentale
Ego)相对应,“此在的结构”与“意向性的结构”相对应,此在的“操劳”(Sorgen)与“我思”(cogito)相对应。从海德格尔的早期讲稿看,他往往一方面讲解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课程,另一方面又在反思胡塞尔的论点和论证是否合理。由此他形成了针对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一整套自己的观点。其中的一个例证就是《时间概念史导论》(1925)。它的五分之二的篇幅是在讲解胡塞尔的现象学,五分之三的篇幅是在讲解他自己的观点,而他自己的观点是针对他所介绍的胡塞尔的观点而展开的。因此,《时间概念史导论》顺理成章地成为《存有与时间》的预备稿。然而,在公开出版的《存有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这种关系隐蔽掉了。但是胡塞尔本人及其当时现象学圈子里的人对此心知肚明。我在以下的评述中,试图把这种关系揭示出来,以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这部艰深的著作。
一、
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问题意识和解题思路之对照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从柏拉图到他那个时代的欧洲2400年的哲学史是以本体论(Ontologie)为主线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史。本体论讨论“存有”(希腊文“on”)的问题。但是传统的本体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把重点落实在“存有者”(Seiendes)的“存有”(Sein)上,而是落实在各存有者中的某个或某些“最高的”或“最基本的”存有者上。他们讨论的不是存有与存有者的关系,而是讨论某个或某些最高的或最基本的存有者如何产生一切其他的存有者。有关什么是最高或最基本的存有者,哲学家们历来众说纷纭,如“物质”、“心灵”、“绝对观念”、“上帝”、“权力意志”等;有的主张只有一个本源,有的主张存在两个乃至多个本源,从而有所谓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之争。本体论的问题本应是“存在论”的问题,但却演变为“本源论”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对存有问题(Seinsfrage)的遗忘,他企图把它逆转过来,即从追问存有者转向追问存有本身。他认为这种逆转是哲学上的一次最重大的革命,将会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如果说海德格尔的第一个问题意识是有关本体论研究的主题的话,那么他的第二个问题意识是有关本体论研究的方法。这时他所质疑的是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的方法论,这包括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方法在内。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问题是把意识与存有分割开来。
如何研究存有呢?必须首先找到一个能够对存有进行发问的发问者。没有这个发问者,一切都无从开始。那么谁是这个发问者呢?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家倾向于把这个发问者当作一个意识的主体。这个主体具有自我意识和理解能力。自我意识被认为是自明的,从自我意识的自明性出发,向存有(实际上是向存有者)发问,是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的基本特征。
胡塞尔的现象学探讨本体论的方式是笛卡尔路线的继续。胡塞尔通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作为意识活动的主体的“自我”的存在。胡塞尔认为意识现象是一种直接的给予;任何一个思者在思的时候,都能直接意识到自己的思的活动、思的内容和作为思的活动的承担者的自我的存在。这种内在的意识具有直接的显现性,因而是自明的。但外部世界中的存在物却不是自明的。这是因为我们直接感知到的只是有关它们的现象,我们无从感知到它们的存在。我们有关外部世界中的事物的存在的观点是一种设定,尽管我们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这种设定具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因此,胡塞尔主张,一方面对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采取存疑态度,另一方面从内在意识的自明性出发探讨各类存有者的本质,即一类存有者区分于另一类的存有者的基本的规定性(基本属性)。本体论的问题就演变为意识主体如何按照存有者的基本属性进行分类的问题。胡塞尔这里所说的属性(Eigenschaft)的含义比较宽泛,它不仅指一事物直接具有的属性,而且包括存有者与存有者之间的关系的属性,以及在关系的关系中的属性。举例来说,原因与结果并不是某个事物直接具有的属性:下雨本身并没有原因的属性,地上湿本身并没有结果的属性;雷电本身没有原因的属性,树木燃烧本身没有结果的属性。但是,一旦我们把下雨与地上湿的关系与雷电与树木燃烧的关系对照起来观看,我们就能看到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因果关系是关系与关系之间的关系。既然下雨与地上湿之类的事件及其关系是存在的,那么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前者是在时空中所发生的存有者及其关系,后者是在关系的关系中存在的存有者及其关系。胡塞尔把前者称为实在的存有者(das reale Seiende)及其关系,把后者称为观念的存有者(das ideale Seiende)及其关系。前者是实质的或区域的本体论(materiale oder regional
Ontologie)研究的范围,后者是形式本体论(formale Ontologie)研究的范围。
把存在与属性区分开来,从向意识直接显现的东西(现象)出发进行哲学研究,包括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基本思路。这条思路的一个前提是,本质与属性相关,但与存在无关;在把存有者(Seiendes)的存在悬置起来之后,照样能对存有者的本质进行研究。海德格尔正是在这里发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的问题。意识现象的存在能与外部世界的存在分割开来吗?当一个人的周围世界(Umwelt)被悬置起来之后,他还能有自我意识吗?“自我”难道不是与“他我”并存的吗?当存在的发问者的在世的存在被悬置起来之后,还能对存在进行发问吗?海德格尔主张,自我的本质不仅在于思,而且在于存在;思不能与存在分开;存在的结构制约思的结构。
海德格尔认为,我所具有的属性是不能独立于我的存在的。当研究物(物理的存有者)的本质的时候,也许可以把它的存在与属性分开,通过找到其基本的属性(基本的规定性)而把握其本质;但是当研究人的本质时,人的存在与本质是分不开的,人的本质在于他的存在:人的本质与其说是一组这样那样的规定性的总和,毋宁说是无,因为人是自由的,自由的要义是无任何固定的规定性。只有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存在及其相关对象的存在采取某种态度和行为的时候,有关一个人的个性才会显现出来。就拿“畏惧”和“勇敢”来说吧,“畏惧”和“勇敢”并不始终表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只有当他处在某种情境中的时候,当某种威胁到他的存在(生存)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存在(生存)采取某种态度和行为的时候(怕死或不怕死,前进还是逃脱),“畏惧”和“勇敢”这两种品性才会表现出来。
海德格尔认为,纯粹从意识出发,是不能从自我达到他我,以及达到外部世界的存在的。离开了在世界中的存在,甚至连自己是什么都弄不清楚。因此海德格尔决定另辟蹊径。海德格尔不想再把自我的纯粹意识当作出发点,而想从一个相对来说最具有直接的自明性的存有者的存在出发。这个相对来说最具有直接的自明性的存有者的存在就是“此在”(Dasein)。每一个存在的探问者最清楚地知道的存在就是他当下的具体存在(此刻此处的存在)。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这种具体的存在误解为具有现存的属性的存有者,而要把它理解为具体的生存,即从无此属性到有此属性的生存,以及将来存在的方式的种种可能性。海德格尔写道:“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所以,在这个存有者身上所展示出来的各种性质都不是‘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现存存有者的现存‘属性’,而是对它来说总是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并且仅此而已。这个存有者的一切‘如此存有’首先就是它的存有本身。因此我们用‘此在’这个名称来指各个存有者,并不表示它是什么(如桌子、椅子、树),而是表达其存有。”[2]从此在出发,探问生存的结构和生存的意义,是海德格尔的新的思路。由此,海德格尔从胡塞尔的“意识哲学”走向他自己的“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
二、此在的生存结构与先验自我的意向性结构
从此在(Dasein)开始探问存在,是海德格尔的《存有与时间》的基本思路。有关此在的含义,要从与自我的对比上去理解。我们知道,笛卡尔、康德、费希特、胡塞尔一路的意识哲学是从自我出发的。这个自我被理解为作为思者的自我。我不清楚外部世界和他人是否存在,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意识的存在。从自己的意识出发,推导出外部世界和他人的存在,是这种意识哲学的基本思路。海德格尔认识到这条哲学路线是错误的。海德格尔认为,自我是一种存有,而不是一种孤零零的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世界中存在。在自我的周围总有其他的存有者。自我是与他我共存的。自我的存在总是具体的,总是存在于不断变化着的时间和空间中。此一刻总是不同于彼一刻,此一处总是不同于彼一处。这是一种活生生的存有,自我不仅亲自感受到这种活生生的存有,而且亲自参与这种活生生的存有。为了避免把自我理解为一种意识哲学中的纯思的自我(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自我,胡塞尔的悬置了世界的存在的“先验自我”),海德格尔制作了一个他的专门的哲学术语“此在”,表示每个人自己的那种亲身活动和亲自能体验到的活生生的在世的存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老一辈的亲炙海德格尔授课的哲学家熊伟把“Dasein”翻译为“亲在”,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说胡塞尔的意识哲学首先是分析意识的意向性结构的话,那么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首先是对此在的结构的分析。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生存具有如下结构:
(1)
此在总是一种寓在(Sein-bei),
(2)
此在总是在操劳(Sorgen);
(3)
此在总是与其他的存有者相遭遇(Begegnenlassen),
(4)
此在总是对其他的存有者采取某种态度和行为(Sich-verhalten-zu)。
对此我们大致可以划出如下示意图:
此在总是与其他的存有者一起存在,在此在的周围总是已经有其他的存有者。当此在与自己发生关系的时候,总是已经与其他的存有者发生了关系。海德格尔把此在的这一特性称为“寓在”。为什么此在总是在操劳呢?因为此在的活动是与生存相关的活动。此在为生存而操劳。此在的这种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活动,而且是一种身体的活动,并常常使用工具。操劳不仅表达了人的意识活动的“认知性”的一面,而且表达了人的意志和情感。因为关系到生存,所以感到担忧,所以要投入行动。此在不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此在势必遭遇到其他的存有者。这种遭遇是不由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自己愿意或不愿意,此在总要与其他的存有者打交道。此在不仅势必被动地与其他的存有者相遇,而且主动地对其他的存有者采取某种态度和行为。不论此在对其他的存有者喜欢或不喜欢,此在总是要与其他的存有者交往,对其他的存有者发出邀请,作出回应,共同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对于此在的“寓在”,与其他的存有者相遭遇,以及对其他的存有者采取某种态度和行为,海德格尔还用“处身情境”(Befindlichkeit)、“被抛”(Geworfenheit)和“筹划”(Entwurf)这些短语来更加形象地刻画。
“处身情境”是一个普通的德文词。它表示(某人)处身于某种情境中,并在这种处境中具有某种感受。从“Befindlichkeit”的构词看,其词干是“befinden”,这有助于表达发现自己的处境,以及感受到自己在这种处境中的心情。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在“befinden”的如下用法中发现:“我们处在一种困难的情境中”(Wir befinden uns in einer schwierigen
Lage);“我们在这里感到很舒服”(Wir befinden uns hier sehr
wohl)。当然,这个词也可用于某物处于某一地点或状况中,但它所强调的是我们可以在那里发现这一物。例如,“
Das Bild befindet sich im
Nationalmuseum”不仅仅表示“这幅画在国家博物馆”,而且强调(我们)在国家博物馆中可以发现这幅画。就表示“存在”而言,“befinden”与“sein”的含义相近。中文“此在存在于世界中”这句话既可翻译为“Dasein ist in der
Welt”,也可翻译为“Dasein befindet sich in der
Welt”。但是,“befinden”不仅表示此在在世的存有,而且表示这种存有是此在自己发现的,与此同时此在感受到自己在这种处境中的心情。由于“befinden”同时具有这两种含义,海德格尔认为通过“befinden”这个词能更生动地揭示此在在世的方式。
此在总是发现自己处身于其他的存有者之间,总是发现自己遭遇到其他的存有者。在此意义上,此在是被动地处身于某种情境中,海德格尔用“被抛”这个词来刻画这种情态。另一方面,此在总是发现自己在操劳,在对其他的存有者采取某种态度和行为。在此意义上,此在主动地应对自己的处境。海德格尔用“筹划”(Entwurf)这个词来刻画这种情态。“被抛”(geworfen)和“筹划”(entwerfen)这两个德文词出于同一个词干“抛”(werfen),正好形成人的处身情境中相对立的两个方面。人的生存就是一方面被抛,另一方面在被抛中进行筹划。因此,海德格尔说:“此在作为被抛的此在被抛入筹划活动的存有方式中。”[3]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结构有别于胡塞尔的意向性的结构。胡塞尔研究意向性结构旨在在意识之内考察意识的活动和意识的内容。海德格尔研究此在的结构旨在表明,此在的生存结构优先于此在(人)的意识结构,此在的生存活动优先于此在的意识活动。胡塞尔通过“意识活动”建立思者与思的内容的关系,海德格尔则通过此在与其他存有者的生存活动建立此在与其他存有者的一种共同的生存的关系。海德格尔的此在是在世的此在,是受到他自己的兴趣、处境、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各种观念影响的。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是经过现象学还原以后的自我。胡塞尔试图通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使其在认识论上获得一种超越的地位,即超脱在世界中养成的自然的心态、超脱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各种观念的影响,超脱个人的喜好、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对自己认识的影响,甚至把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也放在括号中存而不论,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把任何直接给与的东西(纯粹现象)当做认识的可靠起点,为知识的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此意义上,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是超越于世界的,先验自我成了一个在世界之外考察世界的一个认识论上的“极”。意识活动从这个自我极出发,与意识内容相关联,并经由意识内容指向世界中的对象。先验自我及其意识活动和意识内容被认为是具有自明性的内在的领域,而世界中的对象被认为是不具有自明性的超越的领域中的东西。这与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此在在世的生存结构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可以为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的意向性结构划出如下示意图:
先验意识的内在领域
先验自我意识活动
意识内容
三、此在的生存与先验自我的思
从此在的生存出发理解存有的意义,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基本本体论(Fundamentalontologie)的主题。要说清楚这一点,还得从存有(Sein)、存有者(Seiendes)和此在(Dasein)三者的关系出发。传统的本体论研究“存有者之为存有者”,即什么是存有者的本质的规定性。从字面上看,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一切存有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存有。然而,究竟什么是存有的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本体论却从来没有正确地回答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找到过一条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途径。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此在出发理解存有的意义,是一条唯一可行的途径。因为,此在是一切存有者中唯一的一个能理解存有的意义的存有者,此在通过它自己的生存(Existenz)理解存在。在生存中,人势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自己的存有和周围的存有采取某种态度和行为,并通过这种活动理解存有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对存有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此在的存有的规定性(eine Seinsbestimmtheit des
Daseins)。”[4]
既然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家把本体论视为对存有者之为存有者的研究,而海德格尔认为这一研究的前提或基础是理解存有的意义,而要理解存有的意义必须从此在着手,通过对此在的生存的领悟把握存有的意义,所以他就把这项研究称为“基本本体论”。
海德格尔把此在的存在称为生存(Existenz)。此在的存在(生存)是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存在,是一种需要自己筹划和照料的存在,是一种委托给自己和需要自己对此负责的存在。此在是在这种对自己的生存的关系中理解存有的意义。
此在总是在这种或那种处境中为自己的生存操劳。“操劳”(sorgen)是一个常用的德文词[5]。海德格尔选用它作为此在生存论建构中的关键概念,因为它涉及身心两个维度,关乎知情意三个层面。在操劳中存在意识的活动(关心、挂虑、担忧),在操劳中存在身体的活动(照料、料理、操办)。操劳把身心的活动统一起来,刻画了人的生存活动的基本特征。以“此在的操劳”代替“我思”(cogito)有利于克服胡塞尔的那种以纯粹意识为重心的现象学。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此在的生存与两类存有相照应:一类是“手边存有”(vorhanden sein),另一类是“应手存有”(zuhanden sein)。“应手存有”是已经与此在打交道的存有,“手边存有”是可能与此在打交道的存有。举例来说,我手边有一张纸,如果它还没有与我的实践目的相关,它就处于在我手边存有的方式中。我可能看见它,也可能没有看见它。由于它离我很近,我很容易发现它,并用它来实现我的目的。这时它对我而言就处于应手存有的方式中。我用它来写字,它就成为书写的纸;我用它来包东西,它就成为包装纸;我把它扔在垃圾箱里,它就成为垃圾。只有当一个存有者处于应手状态中时,它才对我真正显现出它是什么。“应手”并不意味一定要拿到手上,或一定要在手上运作(上下手),而是指成为我们的实践活动的相关项。举例来说,我们不可能把太阳拿到手上,但我们可以用太阳来计时和晒衣服,这时太阳就成为我们的应手存有的用具,它以应手存有的方式向我们展开。海德格尔写道:“任何操劳所及的工件不仅在工场内的世界中是应手存有的,而且在开放的世界中是应手存有的。随这一开放的世界,周围世界的自然被揭示了,并成为每个人都可通达的。在小路、大街、桥梁、房屋中,自然都是随着操劳活动的一定的方向而被揭示的。带顶篷的月台考虑到了风雨,公共照明考虑到了黑暗,也就是说,考虑到了日光的在场与不在场的特殊变化,考虑到了‘太阳的位置’。”[6]
海德格尔强调我们总是在生存中认识存有者,认识依赖于实践的兴趣。当此在指向某个存有者时,此在是在实践中与某物相关联的。海德格尔使用“应手存有”的概念,是为了突出存有是在我们的实践中向我们展开的,是适应于我们的实践目标的。我们的应手存有的方式是什么,决定了我们所认识的存有者是什么。实践相对于认识而言,具有优先性。严格地说,当某物仅仅在手边存在时,即当我们还没有把它与我们的实践兴趣相关联时,我们无法说它是什么。某物在手边存有是某物的应手存有的可能性条件,从而是我们认识某物的可能性条件,但还不是认识某物的充分条件。纯粹的手边的某物,由于我们还说不出它是什么,只能当做应手的某物一个边界概念(Grenzbegriff)来把握。
对于海德格尔有关“应手存有”的意义,我们最好结合胡塞尔的现象学来理解。在胡塞尔的前期哲学中[7],对存有者的本质的认识是以先验自我的直观为基础的,在此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被悬置起来。这样,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就无从谈起。海德格尔强调“应手”在认识中的作用,强调人带着实践的兴趣认识事物,就在于揭示胡塞尔的这种直观认识论的弊端。胡塞尔所说的通过本质直观认识事物,仿佛只是在静观“手边”的存有者。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果一个存有者不应手(脱离我们的实践活动),我们甚至说不出它究竟是什么。只有当一个存有者从手边的存有方式(Vorhandenheit)转化为应手的存有方式(Zuhandenheit)时,真正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认识活动才发生。海德格尔写道:“这些存有者的存有的方式就是应手方式。……应手方式是存有者自身的存有在本体论上具有特征性的规定性。”[8]
四、此在的生存的时间与内在意识的时间
海德格尔从此在的生存的角度阐明时间,胡塞尔则从内在意识的体验的角度阐明时间。
海德格尔有关时间的中心观点是:“时间性绽露为本真的操劳的意义。”[9]
操劳是对可能性的操劳,是对将发生的事情的操劳,是对生存的操劳。在操劳中,我们可以发现时间性。操劳是现在的活动,操劳所指向的是将发生的事情,操劳所依据的是过去的经验。因此,操劳是现在、过去和将来的统一。时间性体现在操劳中。但是在操劳中,我们未见得总能体验到时间性。在我们为日常琐事忙忙碌碌的时候,在我们随波逐流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时间在我们身边白白流逝。只有在那种本真的操劳中,即只有当此在意识到是在为自己的生存的可能性而操劳时,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展开将以死亡为终结时,此在才意识到时间弥足珍贵。
在此在的结构中已经体现出时间的结构。此在是当下的活生生的在场(Anwesen);此在被抛入当下的处境中,此在的被抛是一种由过去(Gewesen)到现在的态势;此在的筹划是一种在被抛中力图有所作为的指向未来(Zukunft)的态势。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过去的各种因素造成的,在现在中凝聚过去的一切,我们的筹划依据过去的经验,旨在改变将来的生存状况。因此,在此在的结构中就可以看到时间性。时间就是此在的生存方式。“操劳结构的原初的统一在于时间性。”[10]
我们从自己的生存中理解时间。时间与我们的生存是合二为一的。当我们理解了自己生存意义的时候,我们也就理解了时间的意义。时间不是某物,时间也不是过去的某物、现在的某物和将来的某物的总合。时间体现在生存中,在生存中包含现在、过去和将来三个维度。在生存的每一瞬间(Augenblick)都能体验到时间。在做出决断的一瞬间,推离过去的一切,同时开启将来的可能性。知道一万年的人不等于就懂得了时间,知道一瞬间与自己生存的关系的人才真正懂得时间。
以往的形而上学在解释时间的时候,不是把时间与存有联系起来,而是把时间与存有者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时间与物体运动的关系,认识到客观的时间以物体在空间中的匀速位移来度量。奥古斯丁认识到内在的时间是意识对在场的东西的知觉,对过去的事情的回忆和对将来的事情的展望。胡塞尔从对意识之流的体验出发解说内在的时间意识。他认为奥古斯丁对时间的解说还不够确切。因为对在场的东西的知觉,对过去的事情的回忆和对将来的事情的展望都可以有停顿。我并非总是在注意在场的东西,我并非总是在回忆过去的东西和展望将来的东西,而时间是一种不停顿地流动的。胡塞尔从有关“知觉场”的心理学的发现中得到启发。他认为“知觉场”包括原初印象(Urimpession)、持留记忆(Retention)和连带展望(Protention)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紧密关联。原初印象居知觉场的中央,它周围是持留记忆和连带展望的晕圈。每一原初印象总是挟带着一种展望,并随即在持留记忆中逐步消退下去,新的原初印象紧跟着占据知觉场的核心。原初的时间意识就是在对这种流动着的知觉场的体认中显现出来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些时间理论都没有切中时间的关键。时间的关键不在于客观的物体,也不在于主观的意识,而在于存有本身;只有在此在的生存中,在此在的本真的操劳中,才能体验到原初的时间。
五、本真的生存与意识的自明性
海德格尔主张,只有在本真的生存中,我们才能认识真理;因此,本真(Eigentlichkeit)是真理(Wahrheit)的前提。
真理常常被理解为命题符合事实,主观的思想符合客观的实在。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真理论是静态的,是背离真理的实质的。我们如何知道命题符合事实,主观的思想符合客观的实在呢?这需要对命题和思想进行检验。检验不是静态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实践活动。当我们说真相大白的时候,真相不是停在那里不动的,而是被揭示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进行揭示,真理就不会向我们显示。因此,此在的揭示活动是真理之为真的前提。我们是在生存中进行揭示。我们的操劳带领我们对现存的意见进行质疑,对遮蔽的东西进行解蔽,对隐藏的可能性进行开发。因此,海德格尔说:“揭示活动是在世的一种方式,巡视着的操劳或甚至停下来观察的操劳都揭示世内存有者。世内存有者成为被揭示的东西,只有在第二位意义上才是‘真’的。原本就‘真’的,亦即进行揭示的,乃是此在。”[11]
为什么有的人容易发现真理,有的人不容易发现真理呢?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总是进入本真的生存状态中。我们往往人云亦云,把流行的意见当作真理。我们不独立思考,不认真对待生存的可能性,不善于开辟新的境域和发现新的天地,这样真理就不向我们显现。要想使我们看到的事物真,必须首先使我们自己的生存真。真理面向人的本真的生存,真理在人的本真的生存中被揭示出来。
然而,此在可以本真地生存(eigentlich existieren),也可以非本真地生存(uneigentlich existieren)。在非本真的状态中,此在把自己理解为像其他的存有者一样的存有者。此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存的可能性,没有领悟生存的意义,而使自己沉沦到物的世界中去。我把自己混同为常人,别人怎么生存我也怎么生存。我随波逐流,把支配自己的生存可能性的决断交付给流行的意见和习俗。别人追求时髦,我也追求时髦。我整天忙忙碌碌,却不知道究竟在为什么忙碌。这样,我就失去了此在的本真性,即那种自己对自己的生存的自我决断和自我负责的精神。在本真的状态中,我意识到自己的此在是一种能在(Seink?nnen),即一种能筹划自己的生存的可能性的存有者。此在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存有者,正是因为此在把生存的可能性抓在自己手里。纵然此在不能为所欲为,此在不得不在被抛中进行筹划,但此在不能放弃这种决断的自由。此在若放弃这种自由,是对存有的亏欠,是要受到良心的谴责的。因为世上一切存有者中唯有此在是那种能进行自由决断的能在。存有把那种能力赋予我,我却没有用好它,我就对不起存有。我的良心之所以要受到谴责,不是因为我不能做,而是因为我能做而没有做。本真的生存并非刻意要使自己的生存标新立异,而是不忘记自己是一种能在,自己要对自己的生存负责。
为了意识到此在的本真的生存,除了要认识此在与其他的存有者的区别之外,还需要认识死亡是此在的终极的可能性。任何此在必有一死,死亡是此在能够先行预料到的结局。“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可能性。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之前。”[12]当此在时时想到终有一死时候,就会珍惜自己有限的时光,对自己的生存负责。常有这样的人,当他临近死亡时,才发觉自己有许多值得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此在的本真性才在他眼前显露出来。
在此在的有限一生中面临种种决断。当有什么事情向我袭来的时候,我可能害怕它而逃跑,我也可能留下来勇敢地面对它。我评估它是否正义,我决心改变不公正的情形。面对强暴,我可能屈服,我也可能为对抗它而献身。当我说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意义不是体现这件事情是什么上,而体现在我的决断和行动改变了生存的处境。此在在决断和行动中造就自己,此在因自己的决断和行动赢得生存的意义。
但是,深受自己的有限性的束缚,深受个人利益的左右,易受常人意见影响的人,是否真的能靠自己的决断成为一个本真的此在呢?对于这一点海德格尔的思想后来发生了动摇。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在《存有与时间》中在有关如何达到本真的此在的问题上,海德格尔的论述相当乏力,这使得他发觉难以仅仅从此在出发探明存有的意义和真理。海德格尔在1930年发表的《论真理的本质》标志着他的思想之路发生一个转折(Kehre)。如果说海德格尔前期哲学的重心是从此在的生存出发阐明存有的意义,那么他的后期哲学的重心则是让存有启明此在的生存的意义。如果把这个问题联系到人道主义,那么他的前期哲学被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解读为一种以人(特别是以个人的生存)为中心的存在主义的人类学或人道主义的哲学,他的后期哲学则是对这种误解的澄清。对此,海德格尔本人在《有关人道主义的一封信》(1947)中说得很清楚:“存有对绽出的筹划中的人启明自己。然则这种筹划并不创造出存有。此外,筹划根本上却是一种被抛的筹划。在筹划中抛者不是人,而是存有本身,是存有本身把人发送到了那种作为其本质的此-有的绽出-生存的状态中去。天命作为存有之启明而发生,作为存有之启明而存在。”[13]
有关海德格尔后期哲学的问题,我在这篇文章中不想探讨了。我在此只想就真理的问题与胡塞尔的相关观点做个比较作为全文的结语。胡塞尔主张,为了获得真理,必须进行现象学的还原,从而使自我成为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使事物本身不受歪曲地显现出来,使纯粹现象原原本本地描述,使知识有一个可靠的起点。所谓先验自我就是这样的一位认识论上的理想的观察者。先验自我要使自己超越于世上的各种利益和意见的纠缠。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的先验自我是没有的,因为一切此在都是在世的此在,一切认识都以生存为本体论上的基础。就这一点而论,我觉得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驳斥相当透彻。不过,海德格尔自己的真理学说也遇到问题。要想使我们认识存有的真理,必须使自己成为本真的此在。然而,要想使自己成为本真的此在,必须接受存有的启明,聆听天命的召唤。这时海德格尔的哲学陷入神秘主义。为什么胡塞尔相信能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达到这样的一个先验自我呢?因为他相信理性的力量。尽管任何人作为“人格的自我”(personales Ich)必定生活在世界上,从他的生活世界出发进行认识,但是当一个人有志于从事彻底的哲学思考,为普遍的知识建立牢靠的“阿基米德点”的时候,他可以凭借理性的力量,超越“自然的心态”,成为一个“先验的自我”。为什么海德格尔相信此在能聆听存有的呼唤呢?因为他相信“天命作为存有之启明而发生,作为存有之启明而存在”。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具有宗教的维度。
[1]
参见Martin Heideggert,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zer Verlag (Neunzehnte Auflage), , S. V.
中译本参照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的《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扉页。有关
“Sein”、“Seiendes”、“Dasein”、“Ontologie”这几个德文词的中文翻译,在中国学术界颇有争议。陈嘉映、王庆节把它们分别译为“存在”、“存在者”、“此在”、“存在论”。王路、俞宣孟主张把它们分别译为“是”、“是者”、“此是”、“是论”。王路、俞宣孟的基本理由是“Sein”的含义要比“存在”丰富,它不仅表示“存在”,而且表示具有这样或那样的规定性(属性、特征、状态、关系、行为、倾向等)。如在“上帝存在”,“地球存在”,“这个杯子是银做的”,“这本书是我的”的4个句子中,都用到“Sein”的第三人称单数“ist”,但它的意思都不一样,有的是在表示“存在”,有的是在表示具有某种属性,处在某种关系中等。我认为,这两种译法都有缺陷。前者的缺陷是中文“存在”不含有“是”(表示具有属性、关系等规定性)的意思,后者的缺陷是中文“是”不含有存在的意思。中文“是”几乎没有单独作为谓词使用的。在“谁是谁非”的句子中,“是”不是表示“存在”,而是表示“正确”或“有理”。我觉得有一个中文词“有”比起“存在”和“是”更接近“Sein”,因为“有”不仅表示“存在”,而且表示具有这样或那样的规定性。我们可以问:“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地球?”。说“有上帝”,“有地球”,与说“上帝存在”,“地球存在”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杯子是银做的”表示“这个杯子有银做的属性”,“这本书是我的”表示“这本书有属于我的关系”。而且,“有”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重要哲学概念,它出现在中国经典的哲学著作老子的《道德经》中。据我所知,在《道德经》的众多德文译本中,这个作为哲学概念的“有”大都被翻译为“Sein”。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大哲学家》中专门阐释过老子。他引述的《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有生于无”是这样翻译的:“Das Sein entsteht aus dem
Nichtsein.”(参见Karl Jaspers, Die grossen Philosophen,
München:Piper, 1989, S.905.)
他还引述了“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一章,认为它的要义是“道的无是那种使得有者(das Seiende)成为有(Sein)的无”。(参见Karl Jaspers, Die grossen Philosophen,
München:Piper, 1989,
S.903.)据说海德格尔与中国学者萧师毅曾合作翻译过老子《道德经》中的一些章节。他们是否把“Sein”翻译为“有”呢?当然这个“有”是与“有者”(Seiendes)相区别的。如能见到他们的德文译本,就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判断。其实,贺麟等中国老一辈的哲学家(如见贺麟翻译的《小逻辑》“有论”),原初大都也把“Sein”翻译为“有”,后来才把“Sein”改译为“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德文“Haben”也译为“有”
,这样两个“有”(作为“Sein”的“有”和作为“Haben”的“有”)容易混淆。为此,我主张把“Sein”译为“存有”,凸显“生存而有”的意思,即首先是生存,因生存而有(这样那样的规定性)。这一译法在台湾学界较流行。相应地,把“Seiendes”译为“存有者”,凸显它是因生存而有这样那样的规定性的东西。按照这一思路,“Dasein”应译为“此存有”,或至少应从这层意思去理解;但这显得有些累赘,所以我仍沿用陈嘉映的译法,把它译为“此在”。由于把“Sein”译为“存有”,就可以把“Existenz”译为“存在”。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翻译不会发生问题。在表述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思想(把存有者的存在悬置起来)时,把“Existenz”译为“存在”要比译为“存有”或“生存”更为贴切。但在海德格尔那里,“Existenz”被用来专指与“Dasein”相关的存在,这时把它译为“生存”更加贴切。“Ontologie”可以译为“存有论”,但考虑到哲学史上出现的相关学说,不仅讨论存有的问题,还讨论对存有者的分类,以及它们的本源问题,所以我遵从较为流行的译法,仍然译为“本体论”。与此相应,“ontisch”译为“本体上的”,“ontologisch”译为本体论上的。我在选用译名时尽可能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根据上下文选用最贴切的,不得已时做必要的辨析,并在括号中加上原文。
[2]
Martin
Heideggert,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zer Verlag (Neunzehnte Auflage), ,
S. 42.
中译本参照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的《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第49-50页。
[3]
Martin
Heideggert,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zer Verlag (Neunzehnte Auflage), ,
S. 145.
中译本参见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的《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第169页。
[4]
Martin
Heideggert,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zer Verlag (Neunzehnte Auflage), ,
S. 12.
中译本参见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的《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第14页。
[5]
“Sorgen”这个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很难在中文中找到一个相对称的译名。它兼具“关心”、“关照”、“担忧”三个含义,并可分别在不同的使用场合突出其中的一种含义。因此,在“sorgen”这个词的实际使用中,有时可以译为操心,有时可以译为操劳。“Besorgen”指具体的操劳或操心,是“sorgen”演化为及物动词的用法。我倾向于把“sorgen”译为“操劳”,主要为了避免只从心理活动的意义上理解这个词,突出它兼具“操心”和‘劳作’这种身心统一活动的含义。我也想把它译为“关照”,把它理解为“关心”和“照料”的身心活动的统一。
[6]
Martin
Heideggert,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zer Verlag (Neunzehnte Auflage), ,
S. 71.
中译本参见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的《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第83-84页。
[7]
胡塞尔在后期哲学中谈到了本体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并提出“生活世界的本体论”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对海德格尔的“应手存有”的概念的吸纳。但胡塞尔坚持“生活世界”只是通向先验现象学的一条道路,“先验意识”仍然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8]
Martin
Heideggert,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zer Verlag (Neunzehnte Auflage), ,
S. 71.
中译本参见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的《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第84页。
[9]
Martin
Heideggert,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zer Verlag (Neunzehnte Auflage), ,
S. 326.
中译本参见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的《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第372页。
[10]
Martin
Heideggert,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zer Verlag (Neunzehnte Auflage), ,
S. 327.
中译本参见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的《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第373页。
[11]
Martin
Heideggert,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zer Verlag (Neunzehnte Auflage), ,
S. 220.
中译本参见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的《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第253页。
[12]
Martin
Heideggert,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zer Verlag (Neunzehnte Auflage), ,
S. 250.
中译本参见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的《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第300页。
[13]
Martin Heideggert, Wegmarken, Frankfurt/M 1967, S.
168。中译本参照孙周兴译的《路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98页。
如果觉得《从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比较的角度解读海德格尔的《存有与时间》》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