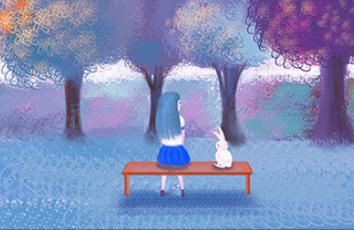BY
朱文颖
朱文颖,生于上海,70 后代表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莉莉姨 妈的细小南方》《戴女士与蓝》《高跟鞋》《水姻缘》,中短篇作品《繁华》《浮 生》《重瞳》《花杀》《哈瓦那》《凝视玛丽娜》等;有部分译为英、法、日、 俄、韩、德、意等文字;曾获国内多种文学奖项;现任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四、素食主义者大卫
大卫是楚玉的第三任伴侣,他差不多要比楚玉大三十岁的样子。
他出现在楚玉生活里的时候,楚玉已经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正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这个异国他乡的临海小城。她的第一任丈夫回到了国内,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她的第二任伴侣麦克,那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只给她留下一些不太愉快的阴影以及一个有着神秘蓝眼睛的小男孩……
在熊炎留下的一叠照片里,我看到过麦克的一个侧影。那时还是麦克和楚玉的蜜月期,他们住在廉租公寓里——据说好像是楚玉出的租金。阳光透过一个凸出的窗户洒进屋里,金光烁烁,恍恍惚惚。
麦克养了一只鹦鹉。那只鹦鹉既不说话,也从不歌唱,它一直就在那些斑驳的阳光里跳来跳去,或者一动不动、发呆。
远处是麦克噼噼啪啪打游戏的声音。
后来,就有了那个混血小男孩。
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混血小男孩。楚玉是如此热爱这个小男孩,天气好的时候,她常常带着他去海边。他是那么轻盈灵巧,他在海滩上奔跑的时候,一头栗色头发闪闪发光,如同一匹金色的锦锻。
有时候,楚玉看着他,不知不觉发现自己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我这是怎么啦?”她问自己,而她的目光则继续追随着他。
她为什么如此爱这个孩子,这是一个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谜。她也爱她的大儿子。这是一个即将成年的少年,个性稳重,沉默而懂事。很小的时候,他便学会了照顾弟弟、母亲,当然还有自己。
离开了暴力的麦克以后,在他乡,这母子三人生活得并不容易——这是显而易见的——或许这也是大卫走进他们生活的原因之一……至少,当画面上呈现出他们四个人的时候,有些东西外人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虽然,这位名叫大卫的加拿大人确实显得年老些,和她并不是那么般配。但是他是爱她的,同时他也爱那两个孩子……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看出那两个孩子也是喜欢和他在一起。
整个画面就是这种感觉,虽然有些部分不免奇怪和不协调。
大卫个子高而挺拔,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他带着楚玉参加附近社交派对的时候,领带偶尔会配错……也不是过于严重的错误,只是使用了与他的年龄不太符合的形状与颜色,款式过于年轻,颜色则太过闪亮与轻浮。其实这种小细节倒是无意中泄露了大卫的一些秘密:早年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有过很多情史,在人类情感方面具有不竭的探索精神……但是不管怎样,他应该是爱着楚玉的。
他喜欢把楚玉打扮成旧上海摩登少妇的样子。猩红的裙子,红唇,鬓角一朵红玫瑰,黑手套,闪闪发光的小包。或许,对于他来说,这些便是他对于中国的异域想象。他需要一个漂亮年轻的女人,一个闪闪发光的令人艳羡的女人,一个有品位的时髦女人。
“你准备好了吗?”他带着楚玉出门以前,常常会兴高采烈地这样问她。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喜悦的,那是一种旁人可能会误解的喜悦。不管怎样,在他的这一生临近尾声的时候,还能够遇到楚玉这样的女子……大卫信上帝,所以他认为这样的奇迹也不是完全不能解释。
在另外一个细节上,我们可以想象大卫对于楚玉的情感。或许因为早年的一些经历,楚玉的有些生活习惯颇为耐人寻味,比如说,她睡觉的时候必须戴着眼罩,而且必须要在一个全黑的屋子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她怕光,同时也怕声音。光让她觉得刺眼,声音则令她感到恐惧。
于是我们能看到一间幽闭的卧室,所有窗帘的缝隙都被仔细处理过了。即便在刺眼的夏日正午,最为细微的光线也被牢牢隔绝在外面;窗帘面料是最厚实紧密的天鹅绒,即便外面雷雨风暴、地动山摇,只要楚玉愿意,她也可以安心地呆在这个小天地里——她可以不再看到,她也可以不再听到。
她可以一直这样地过下去,只要她愿意。她可以躲在这里,坐在这里,躺在这里……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而心情不错的时候,或者略微空闲的时候,她可以走出去,去海边听一听教堂的钟声、海浪的声音。那么多年过去了,她能够听出那里面渗透的安宁。至少那种等候着我们每个人的永恒的安眠,那种东西,从来就不是她害怕的。就像她这个人,在真正的孤独里面,反而没有任何人可以碰到她。
这一切,都是系着错误领带的大卫给她做的。
有一些时候,他们甚至还是欢乐的。
在那些社交派对上,他们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人。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位荷兰艺术家。那位身穿宽松牛仔衣、留着长头发的艺术家告诉他们说,他的第一位妻子来自印度尼西亚,第二位同样来自印度尼西亚,而现在,他的第三位女朋友则是上海人。
就这样,聊着聊着,他们突然谈到了素食这件事。
荷兰艺术家说,他以前吃很多很多肉,但后来他迷上了冥想艺术。他的师傅告诉他,来自胃部的感觉会破坏冥想……于是第二天,这位荷兰艺术家就成了素食主义者。他告诉大卫和楚玉,如果现在他再吃肉的话,第二天身体就会有反应,脸上和后背会长出一片红色的痘痘。
很显然,楚玉是很喜欢这种有趣的谈话的,她甚至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接下来,那位荷兰艺术家又开始说,在中国的时候,他看到好多年轻人在地铁上、火车上看手机、看电脑,那样的时候他经常会想:“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他就换位思考,“如果我坐在这里,这样的时候我会干什么呢?”荷兰艺术家歪歪脑袋说:“哦,我想我会从口袋里把书拿出来。”
在场的几个人微微笑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在中国投资了工厂,常年在两地往返,便很有礼貌地回应道:“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与文化和思想相关的东西也会随之生长。我已经看到中国这些年造了很多庙宇和博物馆……”
紧接着,荷兰艺术家说了几句有点玄妙的话:“我是这么想的,一切外形都是从心里生发出来的。比如说呢,现在我们旁边的这棵树,它的根系从土地里长出来,慢慢地树根开始变细,伸出枝杆,长出叶子。最重要的是,它的内心向往着天空,正是这一切,使它最终成为了一棵树。”
大家沉默了几秒钟,有的人微笑着,有的人歪歪头走到一边找东西吃,还有几个围上去和荷兰艺术家说话……就像这样直接或者间接的关于中国的讨论,零零星星的,总是有。有些时候楚玉会参与,更多的时候她不参与。
很多年前,她决定离开中国的时候,只是因为一种气味。说它是商业气也好,说她敏感也好,说她格格不入也罢,她就是固执地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了,于是就执意离开。或许“错过你之后,一切都是将就?”这个你是谁?是应该快乐而从未真正快乐的童年?是熊炎?是与生俱来的什么奇怪的感觉——就像荷兰艺术家说的,如果现在他再吃肉的话,第二天身体就会起反应?
她也说不清楚。但是,说来也怪,有一件事情却是惊人的巧合。她遇到大卫不久,就发现他是个素食主义者,后来在他的影响下,她也渐渐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有一次,她和母亲通电话,聊了一会儿,她突然明白了什么,问道:“妈,你现在也开始吃素了?”
这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大卫、楚玉以及楚玉的母亲都是素食主义者。在成为素食主义者以前,楚玉真的不能想象,现在,当她重新接触荤腥的时候,她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恶心感觉。她变得如此热爱那些纤弱而羞涩的植物,正是它们,让她天性里某些暴烈而不能把握的东西变得温和起来、舒缓起来……她好像已经忘记了以前的很多事情,仿佛被催眠,又如同冬眠在一个温度和湿度都很适宜的巢穴里……她不再生长,也不再向往,她成了另外一个人。
或许正因为这样,现在,她竟然能忍受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她静静地、微笑着让大卫控制着她的生活:他喜欢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带她去派对,但他绝不让她独自出门跳舞;不能独自跳舞、游泳、见异性朋友、去一些有趣的地方……这一切,她全都微笑着接受了。或许,她早就认为,两个素食主义者的余生也就是这样度过了罢。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就是这样了吧。
她已经累了。那么,能够遇到一个相对温和的素食主义者,就像两株暖阳下细细的孤独的植物……也就是这样了吧。
不止一次,楚玉这样想过。
至于她母亲,那是后来她听重逢后的熊炎说的。在和楚玉重新取得联系以后,熊炎经常会去看望她的母亲,他倒是没有提及素食的事情。熊炎说了另外一个细节。他说,楚玉的母亲现在常去教堂做礼拜,几乎每周都去。他说,有时候提到楚玉,她会哭。那样的时候,熊炎也不说什么,退到一个角落里抽一支烟。等到楚玉的母亲缓过来,他再回去,陪她说话。
熊炎还告诉楚玉说,“你知道吗?你妈妈常去的那个小教堂,就在我们学校的边门旁边。”
楚玉仔细想了想,仍然想不起那扇有着生锈铁锁的边门旁边,有那样一个小教堂。她既没有看见过它,甚至也没有任何关于教堂钟声的回忆。
孩子们
整整十五年后,楚玉带着大卫和两个孩子回国探亲的时候,正是微寒的早春。两个孩子一个十五岁、一个七岁。楚玉给他们两个都起了中文名字,大的男孩小名周周,小的则唤作朱朱。
都是礼貌温文的孩子,长得也好。小的那个显得更娇惯脆弱一些,他瞪大眼睛看着周围新奇的世界,同时又寸步不离地围绕着母亲。他偶尔发呆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圆圆的眼睛像极了那只鹦鹉,在斑驳的阳光里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大的看起来则要平静并且冷漠得多,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懂事。天上零零星星地下起了雨,楚玉的母亲只顾拉着楚玉哭……后来,是熊炎跑去买了几把伞。一共买了三把,先是楚玉和她母亲合撑一把,但是小男孩朱朱一定要挤进来。于是楚玉和朱朱合撑一把,熊炎和楚玉母亲合撑一把。剩下来的一把则留给了大儿子周周和大卫。
相互介绍的时候是这样说的——熊炎是楚玉母亲的干儿子,这话由楚玉来翻译给大卫听。大卫微微地点头,而于西方文化中他并不能理解得非常透彻,也就礼貌地与这位略有些不明身份的男子打了招呼。
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或许只有楚玉母亲真正注意到了,并且能够客观地给予评价。由于国际航班的长途颠簸和本身体质的虚弱,楚玉突然感觉有些不适。于是,她就近找了把椅子坐下来。大卫马上走过去,轻轻搂住了她,并且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熊炎脸上有浅浅的阴影晃过,但明显是克制住了;那两个孩子——周周和朱朱,小的那个紧紧拉住了母亲的手,大的则更多地报以焦灼的眼神……这幅看似极不和谐的画面,却由于楚玉这个焦点的缘故,变得有一丝柔软和温暖的感觉,虽然那种不和谐与紧张感仍然还是存在着。
晚餐是熊炎安排的。无论菜肴的种类还是餐厅的陈设,显而易见都经过了精心选择。餐桌旁边是个小晒台,打开一扇落地的玻璃门,外面就是星空下的一片小小空地。雨已经停了,灰沉的雨云也散去大半,月亮不见,星星却闪闪烁烁地冒了出来。先是朱朱跑了出去,周周也很快跟出去……两个孩子在星空下面变得自在起来,不断有笑声和尖叫声传进来。
楚玉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他们。
这两个孩子……她曾经以为,他们已经成为了她与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她没想到熊炎还会再次在她生活里出现;她也没想到事隔多年,她还会回到这个她以为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地方(她甚至都没有想过教两个孩子中文);她想到妈妈会老,头发白了,腰弯了,眼睛花了,但是她没想到妈妈眼睛里那种星光一样的东西竟然又回来了……有很多东西让她觉得不习惯,让她感觉害羞,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没指望这世界上还会有奇迹发生……
餐桌上,他们三个人吃素:楚玉、楚玉妈妈以及大卫。对于食物,他们安全地选择、规则地分类、淡然地享用。然而熊炎不是。显而易见,熊炎不相信这个世界的一般规则。
他要打破这个规则。
饭吃到一半,熊炎突然离开餐桌,跟随着两个孩子——周周和朱朱去了外面的小晒台。
楚玉的目光一直跟随着他们。
她没想到有一个人的目光也一直跟随着他们和她,那目光不仅仅是怜爱的、柔软的,更是狐疑的、不信任的……
那个人正是大卫。
楚玉、熊炎和大卫
那是回国后的第二还是第三天晚上,具体的情形记不清了,但发生的事情却是确定无疑的:在大卫的一再询问、追问以及最终的逼问下,楚玉告诉了他关于熊炎的真实身份。“他是你的……情人?”大卫的声音里夹杂着颤抖的虚弱和愤怒的强度。
“他只是我的初恋。”楚玉很平静,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见面了。”
“你马上整理东西!马上!现在!”大卫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大卫用力地扬了几次手,仍然不甘心似的,放下,再用心地扬了几下。
楚玉冷冷地看着他。
总是这样,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当她希望平等理性地与他讨论问题的时候,总会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关系中,其实并不存在着平等或者理性。虽然他是爱她的,同时也爱着那两个孩子,但就如同参加社交派对时大卫偶尔搭配错误的领带,细腻敏感如她,总是一下子就探底到了事情的本质:她和他,他们根本就是两类人。他并不懂得人性世界的抽象复杂——他的世界,是款式假装年轻、颜色太过鲜亮轻浮的世界……他甚至连高中程度的教育都没有完成……而她,她是谁?
是的,如果不是熊炎的出现,她也几乎快要忘记她是谁了。在大卫对她和孩子的关爱和床笫的汹涌中,她一度错觉生活其实是可以这样的。她并不需要太多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从来只是让她痛苦。不是吗?但是,为什么,这几天来,她一直回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场景。那是一个初春的傍晚,她,熊炎,还有另外几个同学春游归来,他们突发奇想,躲到了学校小树林深处的一片空地上。夜幕已然低垂,星星开始如同潮水一般云集。
那天晚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星星呢。在楚玉后来的人生中,她几乎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此多的明亮的星辰。
是熊炎说的。他突然说:“来,我们找一块干净的地方,躺下来,仰头看着天上的星空。”
大家还在叽叽喳喳地说笑着。熊炎又说:“快来,只要看过一眼,你就再也无法忘记了。”
于是,他们真的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大家慢慢地躺了下来。
后来,回家的路上,他们几个一句话都没有说。
接下来的几天,大卫开始形影不离地跟着楚玉和熊炎。他就如同一个阴魂不散的幽灵,出奇不意地出现在他们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他甚至还换上了一套深灰色的衣服、一顶深灰色的帽子以及大大的口罩,企图让自己淹没在茫茫无边的人海中。有几次,人地生疏,他毫无悬念地迷了路,然而打给楚玉的电话随即跟踪而至……这样的悬疑片段出现在楚玉旧地重游的园林里、小巷里、拥挤到让人窒息的人流里,直至最终回到冷冰冰的、连桌椅都凸显敌意的宾馆里。
大卫像一头被激怒的兽类暴跳如雷。
因为紧张和忙乱,他完全顾不上系领带以及搭配颜色鲜艳的衣服,风尘仆仆,面容憔悴,却呈现出另一种质朴无助的面貌来。
有一次,他狠狠地喝了两口威士忌,来到楚玉面前,突然一下子跪了下来。“你不要离开我。”他喃喃地说着,灰蓝的眼珠里有着鲜红的血丝。
楚玉愣住了,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你不要离开我。”大卫伸出手,紧紧抓住楚玉的手臂。
楚玉被他吓住了,猛地向后退了几步。
“你要是离开我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大卫的眼睛里缓缓地淌出一行泪水。心里不知什么地方酸楚了一下,楚玉向大卫伸出了手。
几天以后,这只手在机场再次握住熊炎的手,依依告别的时候,甚至还稍稍犹疑了一下。
黑天鹅和白天鹅
回到加拿大后,几乎一夜之间,楚玉发现,原本属于她的一切对外通讯方式都被大卫控制了。
有那么几天,她没法给熊炎打电话、发邮件、写微信,她没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就如同被困在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说来也怪,在她的生活里,每隔一段时间,这种接近于窒息的感受就会出现一次:先是童年的那段伤心时光;再是与熊炎的阴差阳错;第一段婚姻的结束;紧接着,是那些布满阴云、晦暗无光的夜晚……永远漫无边际的漂零……就像故乡暮春的阴天,衬衫衣领上都能闻到雨滴的气味,让人沉陷的气味。
但是,那两个孩子——周周和朱朱,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出现在她面前,魔术般的幻觉总是从天而降。她总是能平静下来,她牵着他们的手,或者他们拉着她的衣襟。她觉得自己突然有了一种飞翔的能力。
还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她带他们去野生动物园。在一片冷清的水域里,奇迹般的一群天鹅缓缓地向他们游了过来。那么慢,那么美,那么平静,同时又是那么忧伤。
他们三个全都呆住了。
“真漂亮呵,那两只白天鹅。”周周忍不住轻声赞叹。
“我……我更喜欢那只黑色的!”朱朱总是喜欢和哥哥对着干,他一边把手里的面包屑朝水面上扔过去,一边不停地叫着:“黑色的!黑色的更漂亮!”
是呵,为什么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楚玉总是能突然穿透现象,直接到达事物的本质。
那天她是怎样向他们解释的?她蹲下身体,紧紧地搂住他们,然后指着镜面一样平静的湖水、丝缎一样亮闪闪的波纹以及童话世界般的天鹅群,她微笑着对两个孩子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美的……”
朱朱一把搂住她的脖子,撒娇地说:“不,黑天鹅美!黑天鹅美!”
周周嘴里也不服气地叽咕着:“当然是白天鹅了,白天鹅更美……”
直到今天,她仍然记得自己的回答,那种瞬间产生的想法。她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美的。颈项的曲线,羽毛的轻盈……所有的天鹅都像一个梦,不管白天鹅还是黑天鹅,它们都是梦,他们都是天使。”
后来,她再也没有带周周和朱朱去过那个水域。有时候她甚至怀疑那个水域是否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中。他们再去野生动物园的时候,经过湖泊区、沼泽区、稀树草原区、森林区、灌丛溪谷区、山地区和雨林区,但是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个同时有着黑天鹅和白天鹅的神秘水域。
它从他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但却牢牢地印刻在她的记忆中。
是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显而易见又相当神秘的——所有那些她不愿意回忆、拒绝回忆、事实上也如同梦魇般的经历,当它们再次以另一种形式回到她的生活、她的思维中的时候,它们全都变成了另外的样子。它们变成了一只只梦境一般的黑天鹅。它们缓缓地向她游过来,不像白天鹅那样洁净、那样明澈;它们游过来的时候,并不是她所期盼的样子,她的心里是带有不安与恐惧的……但是,当她渐渐真正看清楚它们的时候,才突然明白过来,那羽毛的黑色以及颈项的幽深,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另有深意——它们确实是美的,是这个完整世界的不完整的一部分,只是换了一种常人不容易认出的方式。
有时候,她甚至会庆幸,比起一般的常人,她看到过更为广阔复杂的世界,听到过这个世界上稀有的天鹅的鸣唱。
是的,她希望,这一次也会同样如此。
一座临海的房子
楚玉从花市买了大把的鲜花,插在花瓶里。
她煮好了最香甜的牛奶,烤好了面包……
她把屋子里所有的窗都打开,让蜜汁一样香甜的空气流进来。
她坐在淡粉微紫的花丛里,微笑着等待着大卫的出现。
大卫的脸还是苍白的,就像一张空无一物的纸。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张苍白而憔悴的脸,比起他高而挺拔的身材、比实际年龄年轻的长相以及有时过于明丽的衣服款式……比起所有这些看起来光鲜的东西,反倒真实许多。在回国的那些天里,特别当大卫形影不离、如同天上乌云般跟随着楚玉和熊炎,当他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般暴跳如雷,当诸如此类不可理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摇头、都在怀疑,内心都存在着恐惧。但是现在,当楚玉看到大卫那张彻夜未眠的苍白的脸……她仿佛突然看到了这个世界非常柔软的一面。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只是脆弱的、柔软的,希望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
“你真的要离开我吗?”大卫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楚玉的眼睛。
“谢谢你,这些年照顾我和……孩子们。”楚玉轻声地说。
……
这样说话的时候,楚玉的声音也会柔软下来。想起那些用最厚实紧密的天鹅绒做成的窗帘;安静的午后时光,大卫在厨房里为她准备下午茶的点心;那些有点点滴滴快乐的社交派对,有时他们甚至一起仰天大笑起来……在她漂泊的半生中,即便所有的人都不相信、都不承认,但她是相信和承认的:大卫无疑是爱过她的,或许现在仍然还爱着,当然用的是他并非完美的方式。真正的问题在于她——她早就不相信爱了,她放弃了,她觉得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那就这样吧,不要再去挣扎了,一切都是徒劳。她真是这样想的。如果不是这样,她或许不会选择大卫……但是现在,坚定而勇敢的、她命里注定的熊炎出现了。那是她以前错过的,是她真正想要的。更关键的是:熊炎不相信命!这是令她惊喜并且等待已久的,但是另一个结果便是:大卫将成为他们爱情的牺牲品,大卫是无辜的。
那天她和大卫谈了很久,从东方既白直至繁星满天。后来他们都很疲惫了,大卫也表达了他的无奈和理解。那就打电话吧,发邮件吧,写微信吧,只要“让我还能再看到你和孩子们,让我还能再照顾你们一段时间”。
这样柔软的条件没有人会忍心拒绝,于是大家各自休息、各自沉思、各自做梦。两个孩子也显得异常乖巧……一切仿佛又复归原位,一切又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
第二天,大卫出门办事了,楚玉送周周和朱朱去了学校,然后她又去海边坐了会儿。在那里,她遇到了几个小城的熟人,闲聊了几句。来了这么久,她渐渐成为了这里的一道风景,再从风景成为了和背景物融为一体的所在。确实也是,有些时候她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可。她甚至幻想过,如果自己是个男儿,并且生在古代,或许也会成为那种游历山河的人。她比别人想象的要宽阔,她有常人不能理解的另一面……但是,多少年后,她听到了熊炎的召唤,她等待了那么久的……
她要呼应他。
就在这天的深夜,楚玉终于用自己的电脑联系上了大洋那边的熊炎。
“我今天总算又能用自己的电脑给你写信了。下午我去了针炙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泪如泉涌,无法停止。针炙所里的那个女孩看我那么伤心,虽然和我素不相识,不明所以,却对我关怀入微,弄得我有点尴尬。我在所里呆了有一个半小时,才渐渐止住了泪。这几天我都半夜半夜地无法入睡……我在想以后我死了,化成灰,也要和你的灰放在一个盒子里,那我们俩就永远不可分离了。不过,如果你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我们也可以分装在两个盒子里,合葬在一个墓中。这一阵子,不知为什么,有很多关于生和死的想法……”
这样的信件多少有点古典和浪漫主义风格,现在的人多半已经不这样写信了。写信的那个泪如泉涌,读信的那位又是怎样强烈的感受呢。说来也怪,很少再有人会有如此激烈的情绪。大部分人的愿望变得不固执,变得可有可无,可进可退,因为几乎每个人都理性清楚地知道,应该向生活的哪个部分索取和争夺,以及索取和争夺的比例。
但这又是谁说的呢,“我所有做对的事都是冲动的时候做的,理性从来不能创造世界。”不管怎样,那个坚定而勇敢、不相信命的熊炎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他很快给楚玉回信。
在信里,他说了很多话,仿佛隔着如此遥远的时空,他们完全可以毫无障碍地沟通、理解、默契……仿佛她就在他的眼前,写着写着,他甚至可以走到她身边去,扶着她的肩膀,温存一下,亲吻一下,稍稍说几句玩笑话,一转身眼眶却又泛红起来,不忍心让对方看到,别过脸去……
他说他今天又去游泳了,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变得苍老,鬓边有白发,身体也有点发胖了。他在泳池里来来回回地游着,有时候沉在水底下很长时间。他仍然在流泪,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男子,因此完全不能理解这些眼泪是从哪里来的,又为什么如此汹涌,不能停歇……他为什么这么爱她?甚至他能清晰地感到,这样强烈的爱情完全不同于三十年前发生在小树林、清晨的微风以及黄昏的夕阳下的那些……岁月是公允的,她也在慢慢变老,至少是在慢慢变老的过程当中。但是为什么,那些眉眼间细微的沧桑,那些瞬间怅然的眼神,那依然美丽却也在悄然变化的身体,这所有的一切,更让他感受到“爱”这个字真正的分量。这一次,它彻底砸痛了他。
他突然产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他觉得,三十年后的这一次相逢,才是他的初恋,他痛彻心扉的初恋。他的婚姻,他认识的其他女人,甚至是三十年前的楚玉,都是为了这次“初恋”准备的;他整整学习了三十年,直到现在,他的身体开始发胖,他的鬓角开始斑白,他才生平第一次认真地、真正地爱上了一个女人。
接下来在信里,他又开始说。既是对她说,也是对自己说,更是对那种真正砸痛他的东西说,“不管怎样,不管将会发生什么,我都要和你——楚玉在一起。”
在信的最后,或者在信接近最后的时候,熊炎还提到了房子——“我们要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五、故事的三种可能性走向
那仍然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空气里湿漉漉的,我的小小咖啡屋里也是湿漉漉的。
店里没有几个客人。我倚在吧台前,看一本现实与魔幻交相辉映的书。我以比较快的速度翻阅着书的前半部分,也就是现实的那部分。它们通常显得笨重、缓慢却又具备非凡的韧性;而到了更为靠后的那些,它们已经具备了飞翔的能力和速度。人物对话变快,命运则更为戏剧性……我听见书页沙沙翻动的声响。这让我暂时忘记了廖廖无几的客人,生意不佳的现状,平庸无奇的生活本身……我甚至觉得,在某个瞬间,这个平淡无奇的咖啡屋也慢慢地向上升腾起来。
就在这时,熊炎走了进来。
他非常激动地告诉我,明天他就要飞往加拿大和楚玉团聚……我让他坐下,沏茶,促膝,侃侃而谈。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他和楚玉,关于他的生活和楚玉的生活,关于他们的生活,关于和他们有关的他人的生活……谈着谈着,话题变得有趣而漫漶,有很多的可能性缓慢地或者尖锐地涌现出来。有时我们微笑着,有时则皱起眉头,或者猛然被吓住了,“怎么会这样!”甚至有一次,熊炎忍不住叫出声来。
没有人知道生活会按照怎样的逻辑往下发展、走动。或者按照里面的某一种,或者几种平行,或者以另一种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诡异方式。
又有谁知道并且能够说清楚呢?
公主和王子结婚了,
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第一种结局的场景就是那座临海的房子,不过不是春天,而是寒冬。屋里很暖,并且生着炉火。我们先看到楚玉忙忙碌碌地在摆放鲜花和水果。十多年过去了,她仍然很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类型的女人,时光仅仅赋予她们香味,而从不轻易带走她们的颜色。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熊炎的声音。他从卧室里走出来,仿佛午睡刚起。他变得更胖了,有些懒散的样子。真正具有生活阅历的人知道,只有内心安详幸福的人才会有这样慵懒的步伐和体态。
今天楚玉的大儿子要带女朋友回家,这是第一次。窗外天气渐暗,雪花慢慢地飘落下来,纷纷扬扬,落到大海里就消失了;落到熊炎和楚玉住着的这座房子的屋顶上,则一点点地慢慢积起来。一点又一点,一片又一片。
两个人在窗口站了会儿,低头说着些什么。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但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如果这张安宁静谧的图景能够配上字幕的话,或许多年前楚玉的这句感慨将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真正的爱情更美好的东西了。”
朱朱头上的虱子
时针停留在两年以后。
如果用另一种计算的方式,也就是熊炎和楚玉结婚一年半以后。
就在一个星期以前,他们突然发现,楚玉小儿子朱朱头发里长出了很多虱子。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给他理发,剃了光头;再把屋里屋外彻底打扫消毒了一下;被子洗了,拿出去晒……谁知晒到一半的时候,暴雨已至,来不及收回,好好的被子淋得透湿。
乱了整整一天。第二天事情也没有完全转变。剃了头发的朱朱还突然犯起了恋母症,每天晚上会醒来好几次,即便楚玉和熊炎把房门锁了,他仍然用力敲门,所以每天晚上楚玉要醒好几次把他再放回到自己的床上。
熊炎也没睡好,每个人都变得脸色苍白,疲劳不堪。到了第三天,熊炎和楚玉决定暂时分床睡,楚玉和朱朱睡,周周一个人睡,熊炎则睡沙发。
这天晚上半夜的时候,熊炎突然醒了,起来抽一支烟。
天上挂着一弯残月,天幕暗蓝。
熊炎坐在沙发上,一连抽了好几支烟。抬起头,墙上挂着他和楚玉的结婚照。他仍然爱她,爱得很深,但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涌起一丝淡淡的忧伤……就像……就像偶然发现的朱朱头上的虱子吧。
没有钟声的小教堂
时针仍然停留在两年以后。
如果用另一种计算的方式,仍然也是熊炎和楚玉结婚一年半以后。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末礼拜。天气不冷不热,不晴不阴。街边一个尖顶小教堂,有人进去,有人出来,有人在门口不断徘徊。
那天我去得很早。或许老天偷偷了解了我的心愿,知道我潜意识里总想与这平平淡淡、衣食无忧的生活区别开来,偏爱极端的故事和想法……于是它赐予了我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结果却是肝肠寸断,痛苦不堪。我四处求助,最终决定躲进这所小教堂里,向自己流泪,向上帝倾诉。
教堂里的人我基本上不认识,所以我也完全不知道,在我左手一边的第一排坐着沈琳——熊炎的前妻;而在我的右手边最后一排,则站着白发苍苍却又满脸喜气的楚玉妈妈。
沈琳仍然是那个圣洁白玫瑰的形象,小小的、端庄的、衬衫扣子紧紧地扣到脖子下面。只是外面多了一件深灰色的外套。如同岁月蒙尘。但这蒙尘在她身上,仍然有一种受难的庄严和神圣。她低垂着眼睛,向无尽的虚空诉说着什么。如果有人站得和她很近,可以看到她手里攥着一张照片,但照片上到底是谁就看不清了,有人说是熊炎,有人说是她和熊炎的孩子,也有人说那是她自己。
有那么一小会儿,教堂里有一阵细细的哭声,和音乐夹杂在一起,既宿命,又令人不安。站在最后一排的楚玉妈妈却只听到了欢乐的声音,她也在祈祷,为大洋彼岸刚刚传来的喜讯——楚玉和熊炎刚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一个有着和楚玉一样的大眼睛的漂亮小女孩。他们给她起了一个名字:惟爱。
就在我流泪不止、就在沈琳肃穆无语、就在楚玉妈妈喜不自禁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音乐出了故障,突然休止。此刻,只有唱诗班天籁般的声音在教堂里回旋,只听到所有的天使都开始歌唱——
“哈里路亚。哈里路亚。”
六、剧 终
真实的时间。
几个月以后,我去一个热带小岛度假。当我走下快艇,双脚刚触到绵软如水的沙滩的瞬间,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躺在沙滩上,睡了一小会儿。
在岛上的十几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睡觉。只有一种声音是永恒不断的,那就是海浪拍打礁石的哗哗的声音。开始的时候总是那么执着而凶猛,恶狠狠地扑向那些黑色的岩石。慢慢地、一次又一次地平静下来,退回来,积蓄着下一次的力量……
我无数次在这样的海浪声中睡着,然后又醒来,仿佛回到了这个世界的尽头。
有一天中午,正在午睡的时候,一个异样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了。是一条不长不短的短信,熊炎发来的。
“现在维多利亚的宾馆昏睡,楚玉和大卫复合了,住在海边的房子里。我这次来没有申请,她很生气。
一丈之内方言丈夫,她希望我理解她。
她也看出来了,对她孩子好的是大卫。我做不到。
剧终。”
我把手机放下。起床,烧水,沏上一杯咖啡。
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大海,可以看到轮渡和快艇远远地驶来,一些人从上面跳下来,手里提着长长的裙摆,或者高高地挽起裤腿,远远地向这片纯白沙滩的小岛走来。
阳光闪闪烁烁地在海水中跳跃。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人们就在这些时明时暗的块面中行走、游荡、爬行。
我慢慢地喝完杯中的咖啡,走到房间的另一头。
靠墙放着我的行李箱。我把它躺倒,打开。
在箱子的夹层里有两份打印稿。它们有着同样的题目,然而是截然不同的结尾。现在,我把上面那份装订好,封存进一个牛皮信封里……在持续不断的海浪和又一批到达者的欢呼声中,轻轻地打开了那第二份……
刊于《青年作家》06期
转载请告知
青年作家杂志社
新青年 新文学 新阅读
如果觉得《朱文颖:听见天使唱哈里路亚(全文完)》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