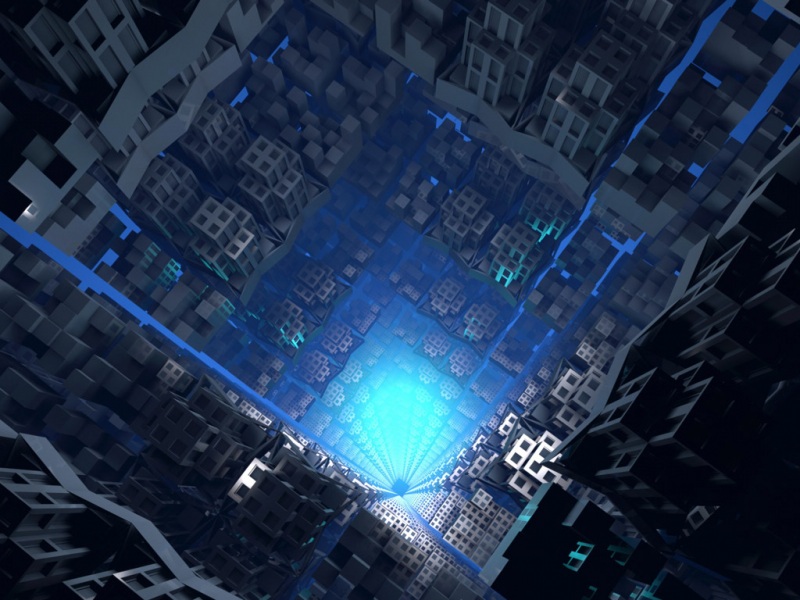张萍博士后的读书心得。
王明珂先生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从人类生态、历史记忆、族群认同等方面对华夏边缘的形成及变迁进行了研究,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王明珂先生介绍了近三四十年以来社会人类学界对于族群现象的理论探讨,以及社会记忆与人类社会群体认同的研究取向在族群现象研究上的新发展。在此研究取向与理论发展背景下,他提出了“民族史研究的边缘理论”,即要研究华夏是如何形成的,中国人为何自称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对华夏边缘的形成进行研究,通过华夏族群的边界,对其中心内涵进行定义。
王明珂先生出生于台湾,师从中研院管东贵研究员及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张光直教授,有着历史学、人类学的双重理论背景,他的研究通常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特别是人类学中的当代族群理论,经常被引入到历史族群研究中。在本书中,王明珂先生反思了客观论、根基论和工具论等当代族群理论,并引入“集体记忆”和“结构性失忆”等概念去重新界定族群的含义。通过对先秦文献、西周铜器铭文所表现出的社会集体记忆与认同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促成华夏我族意识萌芽最重要的“华夏边缘”,应是华夏对戎狄之异类感造成的其北方我族边缘;而战国至秦汉时期,华夏认同与统一的华夏国家形成,同时进行的便是当时人对“历史”的集体回忆、失忆、修订。华夏边缘形成之后,随着华夏的西向、南向扩张,华夏边缘也逐步向西、向南漂移。华夏边缘的向外扩张、漂移包括两个同时并进的过程:一是华夏重新定义谁是异族,一是原来的非华夏假借华夏祖源而成为华夏。
王明珂先生通过族群边缘的视角建构了新的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以勾勒华夏边缘形成的方式来研究华夏概念和华夏族群认同形成的过程,其视角、理论对当时的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对“集体记忆”、“结构性失忆”等当代民族理论的理解与分析,王明珂先生在书中批判了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民族溯源理论。笔者认为,王明珂先生对于族群追溯的传统方法的质疑直到今天仍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他对于考古学中族群追溯方法的质疑,笔者有一些不同意见,有可商榷之处。
一、考古材料与“族群认同”的对应关系
民族理论认为,民族就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新中国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也多参考这一标准。人们对于一个族群或民族的观察、分类与描述,经常脱离不了体质与文化特征,比如肤色、发色、高矮等体质特征,语言、服饰、发式、刺青、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特征。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学者经常以语言词汇、宗教、风俗习惯来探索历史上一个民族的分布范围及其起源。在考古学中,以某些客观文化特征来界定的“考古学文化”也常常被当作是某一古代民族的遗存。以考古学文化来附和古文献上的民族,或以文化特征来追溯其族源是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界的传统做法。
王明珂先生认为,首先,在考古学中并非所有的文化特征都被用来表现族群认同,从考古材料中,我们很难知道哪一种是古人用来表明自己族群身份的文化特征。其次,即使我们能掌握一个人群自我宣示的族群文化特征,从“视状况而定的族群认同(situational ethnicity)”的观点来看,一个族群与不同异族互动时,可能会强调不同的文化特征来排除不同的异族。因此,同一族群的活动,在考古上可能留下不同的文化特征。族群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使得结合历史文献上的民族记载对应考古材料尤为困难。另外,特定文化特征在空间人群的分布,常呈连续性变化,没有明确的边界。或者,不同文化特征所界定的人群,常成为一个个重叠而又不完全相合的圈子,它们与民族边界往往不相符合。他使用了考古发掘中的案例来进行说明,如青海大通发现的一座匈奴砖室墓葬,为双穹隆顶式的墓室结构,并出土蝙蝠形柿蒂纹的铜镜以及五铢钱等,年代在东汉晚期。其墓室结构和随葬仓、井、灶等明器,与中原地区基本雷同,有非常强烈的汉文化因素。王明珂先生认为,如果不是在墓葬中发现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发掘者很可能将墓主人视为汉上层人物。墓葬与窖藏的文物,是有意被人们制造、收集及保存下来的文物,这些器物上所包含的文字铭刻、纹饰图案,蕴含某种社会价值与历史记忆。因此,通过文化特征来断定族群是非常危险的。
考古学文化通常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区域、有共同特征的一类遗存。因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关系,在同一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内,也可能存在着有个别不同的文化单位,但是从大的时空范围来看,这不能改变区域性的文化现象。因此,某个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对应是有一定依据的。而且,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过程中,不同文化因素的出现,往往考古学家需要谨慎地辨别其原因究竟属于文化交流还是文化主体改变,在考古学研究中,这种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往往会结合更大空间的文化交流、聚落形态、葬制葬俗、器物组合等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再得出结论。“汉匈奴归义亲汉长”是汉政府颁发给降服归义的匈奴首领的玺印,青海匈奴砖式墓所发现的汉文化因素既是该匈奴首领对于“亲汉长”身份的认同,也是当时匈奴大规模南迁后受到汉文化冲击,其民族内部组织趋于解体的表现,是边疆民族融入汉族的写照。这个案例不仅不能说明考古文化特征与族源无关,相反恰恰证实了物质文化与族源的密切联系,正是王明珂先生所说的华夏边缘的扩张、“原来的非华夏假借华夏祖源而成为华夏”的某种物质体现。
二、王明珂先生“考古类型学”看法之商榷
王明珂先生在该书中否定了考古类型学的科学性,他例举了一些考古研究中的具体案例,如许多学者以先周考古遗存中的分裆鬲与连裆鬲来划分古文献中的姜姓与姬姓两大部落,并以此追溯周人的族源至光社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或辛店、寺洼文化之中。他认为鬲及鬲的足部特征只是考古学文化所见许多物质文化现象之一,如果我们以其他物质文化现象来追溯周人的族源,可能得到许多不同的结果。另外,王明珂先生还认为,考古学中的物质文化分类有多重标准,考古学家选择不同的器物特征作为新的分类标准,得到不同的“文化”范畴。以考古遗存某些器物的“相似性”追溯这些考古文化特征更早的形态及其地理分布,只能得出其物质文化来源,而与“族源”没有绝对关联。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主要是通过分析遗迹、遗物的形态变化过程,结合地层学,确定其演变的内在逻辑,从而对考古遗存的变化规律、逻辑发展序列以及相互关系等进行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考古学家在运用考古类型学时就更注重多重器物形式变化的共生关系、器物组合的演变等,而不仅仅注重单个器物的演变[2]。并且,器物的形态是受到一定因素而产生变化的,其变化有逻辑的演变。考古类型学是通过科学的归纳、分类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考古学家可能会使用较为主观的分类方法,但事物的内在逻辑是客观存在的,正确的使用考古类型学,就会发现其演变的客观逻辑。考古类型学的科学性已经经受住了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是考古学研究最坚实的理论基础。以考古学文化特征来进行族群的溯源,也许不能完全还原历史史实,但可以更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真相。此外,在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中国当代的民族聚居现象为“大杂居,小聚居”,但是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各族间交叉流动和相互交往的结果。在史前及先秦时期,同一族群的聚居的倾向应该还是非常高的,与秦汉以来长期形成的以汉族为核心、多民族一体的格局有很大区别。因资源、生态所导致的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差异性十分显著,文化与族群的关联也更为紧密,以此进行族群的溯源研究是有价值的。
《华夏边缘》一书将当代民族理论的概念引入到历史与族群研究之中,其民族边缘理论对于我们长久以来的多元统一民族格局认识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其对传统族群理论、考古学、历史学等研究方法的反思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入讨论的价值。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9月,第5页。
[2]苏秉琦,《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第235-237页。
如果觉得《考古学族群溯源方法之思考 ——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有感》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