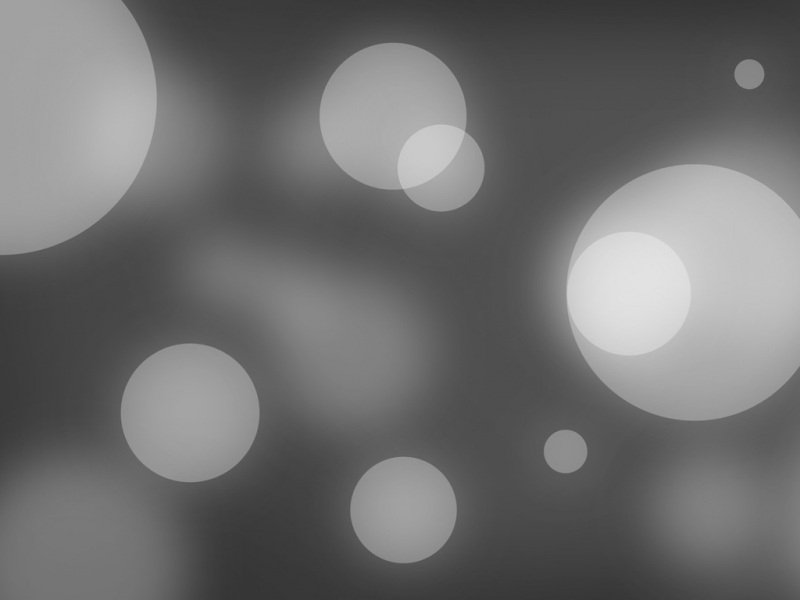一
路易斯·克利德3岁就失去了父亲,也从不知道祖父是谁,他从没料想到在自己步入中年时,却遇到了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事实如此,作为成人,又是年近中年时才遇到这样一位年纪上本可以做他的父亲的人,克利德只好称这位老人为朋友。他是在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女儿艾丽的宠物——小猫温斯顿·丘吉尔,简称丘吉——一起搬进路德楼镇的这所大白房子的那个傍晚见到这个老人的。
起初路易斯开车带着一家人在他将任职的大学附近找他们将搬入的房子,但进展缓慢,就像大海捞针。在他们即将找到那所房子时,所有的界标都对,恰如恺撒大帝被刺身亡的那个夜晚的占星图般清晰。路易斯厌倦地想,大家都已疲惫不堪,紧张烦躁极了。小儿子盖基正在长牙,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胡闹,不管妻子瑞琪儿给他唱了多少支催眠曲,他就是不睡。甚至已经不该给他吃奶了,瑞琪儿还是给他喂奶,可盖基却用他那刚刚长出的新牙咬了妈妈一口。瑞琪儿心里不快,因为她还不清楚从自己熟悉的生在那儿长在那儿的芝加哥搬到缅因州是否正确,又被儿子咬了一口,就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女儿艾丽也立刻跟着哭起来。在旅行轿车的后座上,小猫丘吉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从他们开车离开芝加哥已有三天了,它一直这样。原先丘吉被关在笼子里,可它不停地哀嚎,他们只好把它放了出来,它那烦躁不安的走动真让人心烦意乱。
路易斯觉得自己也要哭了。一个疯狂却很有吸引力的想法突然闯入他的脑海:他准备建议大家回到班格去吃点东西,等等拉行李的货车;当他的三个家人下了车后,他就一踩油门,头也不回地开跑,管它那四缸汽化器会耗掉他多少昂贵的汽油呢。他将开车向南,一路开到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在那儿他将改名换姓,到迪斯尼世界找份工作,做个医生。不过在他开上南部州界95号收费高速公路前,他会在路边停下来,把那只该死的猫扔掉。
这么想着,车子又拐了最后一道弯,直到那时,他才见到了那所房子。在他确定得到缅因大学的职位后,他曾乘飞机来看过这所他们从七所房子的照片中选中的房子。这是一所古老的新英格兰殖民时期建造的房子,不过刚刚装修了,隔热、取暖都不错,虽然价钱贵了些。楼下有三个大房间,楼上还有四个房间。一个长长的遮阳棚,以后也可改建成更多的房间。房子四周是一片草场,即便在这八月的酷暑下,草叶依然茂盛葱绿。
房子的另一边有一大块可供孩子们玩耍的田地,田地的那边是无边无垠的树林。房地产经纪人曾说过,这块地产处于州界,在可预知的将来一段时间内不会被开发。米克迈克印第安部落人的后代在路德楼镇及其东部的城镇占有近8000英亩的土地,错综复杂的诉讼,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也许会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
瑞琪儿突然停止了哭泣。她坐直了身子说:“那就是——” “是的。”路易斯说。他有点不安——不,他觉得害怕。事实上,他被吓住了。他将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抵押在了这所房子上,直到艾丽17岁时,他们才能偿清抵押贷款。
他咽了口唾沫。
“你觉得怎么样?”
“漂亮极了。”瑞琪儿说。路易斯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看出妻子没有开玩笑,在沥青铺就的车道上绕行到后面的遮阳棚时,他看到妻子的眼睛在扫视着窗子,也许她的脑子里在想着该用什么样的窗帘和碗橱上铺什么样的油布了吧,天知道她还想着些什么。
“爸爸?”艾丽在后座上说。她也不哭了。就是盖基也不再吵闹了。路易斯觉察到了那份寂静。
“怎么了,亲爱的?”
艾丽的眼睛在后视镜的反射和深金**头发的映衬下呈现出棕色,她也在扫视着房子、草地、远处另一所房子的屋顶和延伸到树林的大块田地。
“这就是家吗?”
“很快就会是了,宝贝。”路易斯回答道。
“噢哦!”她大叫起来,几乎要震破了他的耳膜。路易斯有时对女儿很生气,不过要是他在奥兰多见到迪斯尼世界的话,他就不会介意女儿的叫声了。
他把车停在遮阳棚前,关闭了发动机。
发动机停了。经历了芝加哥、路普和州际公路上的喧闹后,在一片寂静中,在夕阳西下的傍晚,他们听到一只鸟儿在甜美地歌唱。
“家。”瑞琪儿轻轻地说,她仍在看着那所房子。
“家。”盖基坐在妈妈的膝盖上,自鸣得意地说。
路易斯和瑞琪儿彼此互相看了一下,透过后视镜,他们看到艾丽瞪大了眼睛。
“你”
“他”
“那是——”
他们一起说,接着又一起大笑起来。盖基没注意这些,他一直在吃大拇指。他会叫“妈”几乎已有一个月了,而且看到路易斯他也已经能勉强发出“巴”这个音
了。
但这次,也许只是碰巧模仿,他的确说出了一个字:家。
路易斯从妻子膝盖上抱起儿子,紧紧地搂着他。
他们就这样来到了路德楼镇。
“好了,艾丽,”他说,“够了,那边的人会以为有人被杀了呢。” “可是我疼——”
路易斯强压怒火,默默地走回汽车那儿。钥匙仍然没有找到,不过急救包还在小储藏柜里。他拿了急救包返回来。艾丽见到他,叫得比以前的声音更大了。
“不!我不要涂那种蜇人的东西!爸爸,我不要涂那种蜇人的东西!不——”
“艾丽,这只不过是红药水,而且它也不蜇人——”
“好孩子,听话,”瑞琪儿说,“它只不过——”
“不——不——不——”
“你给我别叫了,要不我打你屁股。”路易斯说。
“她有点累了,路。”瑞琪儿静静地说。
“是,我知道她的感觉。把她的腿露出来。”
瑞琪儿将盖基放下来,把艾丽的裤腿挽上去,按着艾丽的腿。路易斯给她上了红药水,尽管她歇斯底里地不断叫着。
“有人从街对面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了,走到门廊那儿了。”瑞琪儿抱起盖基说。
他刚要从草丛中爬走呢。
“真不错。”路易斯含糊地说。
“路,艾丽她——”
“累了,我知道。”他盖上红药水瓶,严厉地看着女儿说:“好了。伤口并不
严重。别小题大做了,艾丽。”
“可我疼啊!我真的受伤了,我疼——”
路易斯手痒得直想揍她,他紧紧用手抓住自己的腿,控制着自己。
“你找到钥匙了吗?”瑞琪儿问。
“还没有。”路易斯回答,他猛地关紧急救包,站了起来。“我再——”
盖基开始尖叫起来。他不是在捣乱,也不是在哭喊,而真的是在尖叫,身子还
在瑞琪儿的怀里扭动。
“他怎么啦?”瑞琪儿大叫道,慌乱地把孩子搡给路易斯。路易斯想,这就是
嫁给医生的优点之一,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孩子看起来有点紧急情况,都可以把孩
子往丈夫那儿一推了之。“路易斯!他怎么——”
孩子正疯狂地边抓挠着自己的脖子,边狂叫着。路易斯迅速接过儿子,翻过他
的身子,看到孩子的脖子侧面鼓起一个白色的疙瘩。他的连衫裤裤带上有个毛茸茸
的东西在轻轻蠕动。
艾丽本来已经有些安静下来了,这时又开始尖叫起来:“蜜蜂!蜜蜂!蜜——
蜂!”她向后一跳,又被刚刚绊倒她的那块突出的石头绊了一跤,重重地跌倒在地
上,带着疼痛、惊异和恐惧,她又开始大哭起来。
路易斯纳闷地想:唉,这是怎么了?我真要疯了。
“想点办法,路易斯!你不能做点儿什么吗?”
“必须把蜇刺弄出来,”他们身后一个声音慢吞吞地说,“恰当的办法是:把
蜇刺弄出来,然后涂些苏打。疙瘩就会下去了。”这声音充满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口
音,路易斯那疲惫的、混乱的脑子用了一会时间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
路易斯转过身来,看到一位老人站在草地上,他也许已有70岁了,但依然精神
矍铄,身体健康。老人穿着件蓝色薄条纹布衬衫,露着满是褶皱的脖子,脸被太阳
晒得黑黝黝的,嘴里叼着根不带过滤嘴的香烟。路易斯瞧着他用拇指和食指掐灭烟,
仔细地放在口袋里,然后伸出双手,向他们狡黠地微笑着。路易斯立刻就喜欢上了
这微笑,他可不是个易于亲近的人。
“医生,我班门弄斧了。”老人说。就这样,路易斯遇到了乍得·克兰道尔,
一个年纪上本应该可以做他的父亲了的人。
三
克兰道尔说他看到他们一家开车穿过街道来到这儿,接着好像有点手忙脚乱,
所以他来看看能不能帮点忙。
路易斯抱着儿子,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克兰道尔走近了些,看了看盖基脖
子上的肿块,然后伸出一只粗短的、扭曲变形的手来。他的手看上去极其笨拙,几
乎跟盖基的头一样大。瑞琪儿张嘴想阻止,话还没出口,只见老人手指灵活一动,
蜜蜂的蜇刺已在他的手心里了。
“这刺真够大的了,虽不能说是冠军,我猜可也差不多能做条带子了。”老人
说。路易斯大笑起来。
克兰道尔带着那种狡黠的微笑看着路易斯,说:“当然,一只出奇大的蜂王,
不是吗?”
“妈妈,他在说什么呢?”艾丽问。瑞琪儿也大笑起来。当然,这太不礼貌了,
不过没关系。克兰道尔从口袋里拿出一盒柴斯特费尔德牌大雪茄,抽出一只塞到嘴
角,边向这群大笑的人高兴地点点头,边用大拇指的指甲盖擦亮了一支木制火柴。
就是被蜂给蜇了的盖基,也不顾肿痛,哈哈大笑起来。路易斯想,老人总有他们的
诀窍,虽然是小诀窍,但有些相当不错。
路易斯停止了大笑,伸出没托着盖基尿湿了的屁股的另一只手,说:“见到您
很高兴,您是?”
“乍得·克兰道尔,”老人边握手边说,“我想,您就是那位医生了?”
“是的。我叫路易斯·克利德。这是我妻子瑞琪儿,这是我女儿艾丽,让蜂给
蜇了的是我儿子盖基。”
“很高兴认识你们大家。”
“我们本不是要大笑……我是说,我们没想大笑……我们只是……有点儿累了。”
这话又使他叽叽咯咯地笑起来。他觉得累极了。
克兰道尔点点头:“当然,你们都累了。”他看了一眼瑞琪儿,“克利德太太,
为什么您不带着孩子们到我们家坐会儿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抹点苏打,减轻疼痛。
我妻子也很想认识你们呢。她不太出门,最近两三年她的关节炎变得严重了。”
瑞琪儿看了一眼路易斯,路易斯点了点头。
“那太好了,谢谢您,克兰道尔先生。”
“噢,叫我乍得好了。”
突然,传来了汽车喇叭声,接着是发动机熄灭的声音,然后人们看到那辆蓝色
大货车拐了弯,隆隆轰响着开进了车道。
“噢,老天,我还没找到钥匙呢。”路易斯说。
“没关系,”克兰道尔说,“我有一串。克利夫兰夫妇给过我一串钥匙。他们
以前住在你们这所房子里,已经十四五年了。他门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克利夫兰
太太是我妻子最好的朋友。她两年前去世了。比尔去了奥灵顿的老年人公寓。我去
把那些钥匙拿来,它们现在属于你们了。”
“太谢谢您了,克兰道尔先生。”瑞琪儿说。
“别客气,”老人说,“我们一直盼着能有年轻人来做邻居呢。克利德太太,
过马路时要看好孩子们,路上有很多大卡车。”
蓝色大货车的车门一响,从驾驶室里跳下来几个搬家公司的人,向他们走来。
艾丽有点走神了,她问:“爸爸,那是什么?”
路易斯已经开始向搬家公司的人走去了,听到女儿的问话,回头一看,只见田
地边缘,草地尽头,有一条约四英尺宽的平整的小路,环山而上,穿过一丛低矮的
灌木和一片白桦林,消失在远方。
“好像是条小路什么的。”路易斯回答女儿说。
“噢,是的,”克兰道尔笑着说,“是条路,**。以后有时间再告诉你。你
来我家吧,我们一起给你的小弟弟上点儿苏打,好吗?”
“当然想了,”艾丽说,接着又带着某种希望似地加了一句,“苏打蜇人吗?”
四
克兰道尔取来钥匙时,路易斯也找到了自己的那串。原来汽车小储藏柜上有条
缝,装钥匙的小信封掉到金属线架里了。他弄出钥匙,开了门,让搬运工往房子里
搬东西。克兰道尔把另一串钥匙也给了他。钥匙拴在一个旧的、已无光泽了的链子
上。路易斯谢了老人,漫不经心地把钥匙放进口袋里,看着搬运工搬运着那些箱子、
梳妆台和衣柜等等他们结婚十年来积攒的东西。看着这些东西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有的还要丢掉,他想,不过是箱子里的一堆破烂,突然,他心头一阵忧伤和沮丧—
—他想也许是人们所说的想家的感觉吧。
“有点像被拔了根,被移植了的感觉吧。”克兰道尔突然在他身边说,路易斯
有点吓了一跳。
“好像您体验过这种感觉似的。”路易斯说。
“不,事实上我没体验过。”克兰道尔啪的一声擦燃一根火柴,点着支烟,火
焰在傍晚的阴影里闪闪发亮。“我爸爸盖了路对面的那所房子,带来了他的妻子和
孩子。那孩子就是我,刚好生于1900年。”
“那您——”
“83岁了。”克兰道尔说。路易斯松了口气,他不用说他厌恶使用的词了。
“您看上去比83可年轻多了。”
克兰道尔耸耸肩膀说:“不管怎么说,我一直住在这儿。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参
了军,不过,我去的离欧洲最近的地方是新泽西州的贝扬纳。那是个龌龊的地方。
即使在19时,那也是个龌龊的地方。回到这儿我真高兴。后来我娶了诺尔玛。
我在铁路上工作。我们至今仍在这儿。不过就在这儿,在路德楼镇,关于生活,我
已见识了不少。我当然见识过不少。”搬运工们在遮阳棚入口处停了下来,抓着绑
着路易斯和瑞琪儿的大双人床的盒子上的绳子问:“克利德先生,我们把这个放在
哪儿?”
“放楼上……等一下,我带你们上去。”路易斯向他们走去,接着停下来回头
看着克兰道尔。
“你上去吧,”克兰道尔微笑着说,“我回去看看你的家人们怎么样了,然后
送他们回来。我不打扰你了,不过搬家真是件令人口渴的工作。我通常大约9点坐在
门廊里喝几杯啤酒。暖和的天气里我喜欢看着夜幕降临。有时诺尔玛和我一起喝点
儿。要是你愿意,你就过来吧。”
“好吧,也许我会来的。不过,别专门来找我,也别熬夜等我——我们今天真
是乱透了。”路易斯说,他其实根本不想去。因为接下来肯定会让他在克兰道尔家
的门廊里给诺尔玛诊断一下她的关节炎,当然是非正式的和免费的了。路易斯倒是
很喜欢克兰道尔,还有他那狡黠的笑、那随便的谈话方式和那美国南方佬的口音。
这种口音一点儿都不僵硬,而且很柔和,像是慢吞吞地唱出来的。是个好人,路易
斯想。但是,医生们对人总是好猜疑。这很不幸,但迟早就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也要
向你求医问药,老年人就更没完没了。
“只要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来,不需要请柬就行了。”克兰道尔说,在他那狡
黠的笑里,路易斯觉得有种东西使他感到克兰道尔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克兰道尔走起路来腰板挺直,步子轻快,像个60岁的人,而不是80多岁的人。
路易斯第一次对老人有种淡淡爱的感觉了。他看了老人一会儿,然后和搬运工一起
上楼。
五
到晚上9点时,搬运工们走了。筋疲力尽的艾丽和盖基都在自己的新房间里睡着
了。盖基睡在他的儿童床上,艾丽睡在一张床垫上,周围放满了箱子、盒子,里面
装着她的无数的克莱奥拉丝娃娃,有的完好无缺,有的已破损了,还有的反应已不
灵敏了。箱子、盒子里还有她的芝麻街招贴画、图画书、衣服等等,天知道还有什
么。当然小猫丘吉也和她在一起,一边睡着一边喉咙里发出刺耳的呼噜声。这刺耳
的呼咧声越来越像只大公猫满足时的呜呜的叫声。
下午刚开始搬东西时,瑞琪儿抱着盖基不停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打量着路易
斯让搬运工放家具的地方,不满意的地方就让他们重摆。最后大货车终于卸完了,
路易斯从胸前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支票和5美元一张的一些小费,给了他们,签了收
据,站在门廊里,目送他们向大卡车走去。他思量着这些人可能会在班格停一下,
喝点啤酒,去去风尘。此时喝点啤酒正合适。这使他又想起了乍得·克兰道尔。
后来,路易斯和瑞琪儿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他看到妻子的眼眶周围的黑晕,
说:“你,去睡吧。”
瑞琪儿笑着说:“是医生的命令吗?”
“对。”
“好吧。”她站起来,说:“我累坏了。盖基晚上很可能会醒了不睡。你也来
睡吗?”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还不想睡,街对面的那个老人——”
“不是街,是路。在乡下,人们叫路。要是你是乍得·克兰道尔,我想你会说
成是‘乐’。”
“好吧,‘乐’对面的老人。他请我去喝杯啤酒。我想我该接受这邀请。我也
累了,可太激动了,睡不着。”
瑞琪儿笑了:“那你就会以听到诺尔玛·克兰道尔告诉你她哪儿疼,睡在什么
样的床垫上告终。”
路易斯大笑起来,一边想,多可笑,多可怕,妻子们总能看出丈夫们在想什么。
他说:“我想,我应该帮他个忙。我们需要帮忙时,他来帮了我们。”
“平等交换?”
路易斯耸耸肩膀,不愿意也不敢肯定怎样告诉妻子自己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已经
喜欢上了这个老人。“他妻子怎么样?”
瑞琪儿说:“性情很温和。盖基竟坐在她的膝头。我很惊讶,你知道,今天儿
子不舒服,而且他一般很难短期内喜欢上个生人。她还给了艾丽一个洋娃娃玩儿。”
“她的关节炎严重吗?”
“很严重。”
“她坐在轮椅里?”
“没有。不过她走路很慢,她的手指——”瑞琪儿举起自己纤细的手指,弯曲
起来模仿成爪子模样。“不管怎样,路易斯,你别在那几待得太晚了,我在陌生的
房子里总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路易斯点点头,亲了她一下,说:“这房子不久就不陌生了。”
六
路易斯回来后觉得自己度量真小。没人让他给诺尔玛·克兰道尔检查身体,他
穿过马路去老人家时,老太太已经睡去了。乍得坐在摇椅上,抽着烟,火光一闪一
闪像夏季里的大萤火虫。收音机里传出低低的红袜子游戏的声音。这一切使路易斯
感觉像到了家一样。他敲了敲门廊的门。
“进来,是克利德医生吧。”克兰道尔说。
“希望您说的关于喝啤酒的事是真的。”路易斯边回答边走了进来。
“噢,关于喝啤酒我从不撒谎。请人喝啤酒撒谎会树敌的。请坐吧,大夫。我
再多加点冰块。”
狭长的门廊里安置了几张藤椅和藤条做的沙发。路易斯坐下来,惊奇地发现非
常舒服。在他的左侧有一个锡桶,里面装着冰块和几罐黑莱贝尔牌的啤酒。他拿了
一罐,边打开边说:“谢谢。”
他喝了两口,觉得沁人心脾。
“多喝点儿,”克兰道尔说,“希望你们在这儿生活愉快,大夫。”
“但愿如此。”
“对了,要是你想来点饼干什么的,我可以给你拿些来。我有一大块准备好了
的莱特奶酪。”
“一大块什么?”
“莱特奶酪。”克兰道尔的话听起来有些暗自好笑的味道。
“谢谢了,不过有啤酒就行了。”
“好吧,那我们就只喝啤酒。”克兰道尔满意地打着嗝说。
“您妻子去睡了?”路易斯问,一
如果觉得《关于斯蒂芬金的小说《宠物公墓》》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